【黑地方】我爸
我爸当了三十多年教师,退休后大感失落,长吁短叹地。我妈说,一个破教导主任,不干就不干了,损失啥了!我爸说,是失落,不是损失。我妈说,文人多作怪。我爸说,当年写信给你时,你咋不说文人多作怪啊!我妈连忙装糊涂,跑去饭桌弄她的钱盒。
一个带钥匙的铁皮盒,是我们家的杂货店收钱用的盒子,晚上我妈会带回家。我爸仍不放弃。你写给你的诗呢,还记不记得,背给我听听。我妈当然估计是记不得了,只顾低头数钱。她一数钱,房子塌了都不知道,完全屏蔽,这倒是真的。
我妈电话给我,说你爸现在烦得很,成天哭哭啼啼的,还想把我也变成小姑娘,跟他一起哭哭啼啼。我劝我妈,三十多年工龄工作一下没有了,整个人都没事干了,不抒个情你让他干啥啊。我妈说,我还有正事得嘛,你让他别缠着我。于是我劝我爸,钓鱼啊,养花,要不你搞写作吧老爸。你不是写过小说吗?捡起来写写吧。
我爸吃惊道,你咋知道我写过小说!哈,我说,我偷看了老爸的日记。你偷看我日记,我也要偷看你的日记,然后我就看到了你写的小说。
我是支持小孩子也有隐私的,没偷看。他还想抵赖,不过并不彻底,因为他接着说。你日记都是我教你写的,我检查一下写得好不好,正大光明的嘛。当年你都是主动给我看,还拿到班上去念,巴不得人人都看。
我说,那是十四岁以前的事,后来我的日记不想给人看了,你就偷看。电话那头传来我爸的嬉笑。十四岁,我晓得,林小梅,嘻嘻。所以嘛老爸,咱们大哥不说二哥,我模仿他的嬉笑,老爸,成都女知青,嘻嘻。
他压低声音,千万千万别给你妈晓得。当然,我说,所以我才不只是偷看老爸的日记,而是偷了老爸的日记。这本日记你肯定是要藏着不给我妈晓得嘛,还不如我帮你藏好了。
我爸问,你带走啦?我说,我上师范校的时候带到师范校了,我当时真怕老妈看到。你再会藏也经不住老妈翻箱倒柜的能力强,我当时想,带到师范校是万无一失。做得对,他夸赞道,后来呢。
后来,我犹豫着不太想说,但也不得不说了。后来,老爸你晓得我1989年烧书被处分的事吧,我把我所有的课本和日记包括你的日记放一把火烧了。不好意思,老爸。烧了也好,他说。
然后,长时间的静默。电话交流的尴尬出现了,看不见表情和肢体,没法再提话头。但彼此肯定知道,交流并未结束。手里的电话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如果这会儿我跟老爸面对面呢?我想。坐在有蓬天竺葵的茶几两边,我爸估计会伸手抚抚天竺葵的叶子,放回鼻子跟前闻一闻。我会说,天竺葵的气味无法形容,这是一种印度的气味。应该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他教我写观察日记时说过的一句话。他应该会很开心地回应说,对,你将来要去一下印度,你们这一辈,要比我们走得更远。
如果茶几上放的是一盆太阳花呢?太阳花喜欢太阳,极度厌恶下雨天。淋雨花瓣就烂掉。下雨天太阳花就会从阳台移到屋里。那么这一次,我和老爸坐在茶几跟前的氛围是个下雨天。下雨天他会起身将电视机打开。这似乎成了他习惯。下雨天不出门,休闲感随雨声而产生。是这个意识让他打开电视机的吧。一种说不上是动机,算不得念头的意识。休闲感,电视机,然而我们还继不继续讲他以小说的形式写日记的事呢?
他一定是非常想写,又怕写了我妈看见不得了。就改了自己的姓名、我妈的姓名,以备将来狡辩说写的是小说而非日记。
小说是虚构的,虚构的就是假的,估计他还会对我妈讲解一番写作知识,当了三十多年中学语文教师,习惯了。
我爸没选晚年稿写作,选了钓鱼。
起初在镇外渔户池塘找点感觉,有把握后到金沙江边钓。
他早饭后从家附近公交站上车,赶过十多站地儿到黄磷厂站。黄磷厂污染大,当初设计就是要避开市民,巴不得建到凉山州的鹿县城去。鹿县城人大为不满,产生了纠纷。终于在2012年左右吧,黄磷厂废除了。只剩空无一人的厂房矗立在江峡中,不过要被自然再次消化,应该还需要很多年。
我爸那会儿到了黄磷厂站,还得再顺江走半个多小时才闻不到黄磷味儿。闻不到黄磷味儿了,心情好起来了。眼前是名为渡口的平缓江滩。之所以名为渡口,是古时鹿县城出发的清溪道过江连接茶马道的摆渡处。因要过马帮,索桥、溜桥过不了,只能选平缓地带设渡口。马帮兴旺时,有摆渡筏,还有负责人家。不过我爸那会儿看到的,只是一片无人的江滩了。
高山退得比较远,面前是水流的、沙滩的、土丘的,几道优美起伏的曲线,加上阳光、风,还有并不急躁的水响,心情好得不得了,但这样的风水似乎不适合钓鱼。
大概从古渡口再往下游走近一个小时,随两岸山势越收越紧,人也越来越紧张地走进一条江峡。江水声响得将人都灌满了,难以感觉其他,人的步伐也奇怪起来。有点想逃跑又不甘心的意思。再走,他见到一个峭壁下有一个巨大洄水荡。移到崖边往下,看着看着,弧状洄水流动厉害了,显出房子那么大一个漩涡。
波浪一圈一圈地往里收,咕噜一声巨响,下陷一个大洞。老天,房子那么大的洞。你懂吧,我说的是漩涡中间的洞就有房子那么大。
老天,听清楚我爸的描述,我立刻想起爱伦坡的恐怖小说。老爸,你站悬崖顶太危险了。那是,他说,我头一晕就赶紧跑。
他连连后退,撒腿就跑,跑到看不见漩涡的地方喘气。定了神,忍不住两腿打颤再去崖边往下看。
奇怪,经常是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漩涡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漩涡是幻觉还是漩涡不见了是幻觉?有点分不清楚呢。
下了悬崖,他站在洄水荡边缘一块礁石上,用最大力气往波浪中扔钓钩,再坐下来,费力地从波纹里找出浮漂。浮漂找到了,慢慢等。
低角度近距离地看洄水荡,勉强能让人坐稳。习惯就好了。连续几个小时盯着无穷无尽的波浪看,再起身走动在实地上时,觉得怪怪的。不过也是习惯就好了。一次习惯二次习惯的,老爸说他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这感觉真好,虽然说不清楚到底身上什么玩意儿被换掉了。
他一江钓新手,万万没料到误打误撞到了一绝佳钓鱼处。
江鲢、细甲鱼、耗儿鱼,洄水荡都有,都钓到过。连鼎鼎有名的中华鲟也有,我和钓友就钓到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压低了声音问我,你说我们吃了它这事对不对呢?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主要是没防着他会突然压低了声音说话。
他继续低沉说道,我们在江边把它烤来吃了。
我仍然没反应过来,只好故作惊讶地问,你们真的把它吃了啊?
他重重说道,对。就在江边拣漂木生火,烧熟了就吃。他说这话的声音依旧低沉,咬字很重。因为这低声,我们几乎同时拿眼睛瞅了瞅电视上播音员的脸。那时房间里只有我和我爸,还有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新闻联播播音员的那张脸。
我忘了,这是一次梦。我梦见我和我爸呆在一个房间里还在说这事。
中华鲟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我是在2000年才知道的。2000年成都有个水族馆倒闭,上了报。报上有一句话我还记得:“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中华鲟,竟因为一家企业的破产而死去。”意思是一条中华鲟比一个企业重要。报上还配发了一副照片,那鱼粗糙难看,好像一根想雕出什么的木头,一看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东西。这鱼的重要性让我怀疑起我爸的话来。也许他们并没有钓到什么中华鲟。也许两个老头,钓了一条认不出来的鱼,决定将它当作中华鲟烤了吃,这种事也是有的。
我爸渔获颇丰,吃不完,他又不想送同事。为什么呢?我不太明白,只隐约觉得就像他又在写一本不想给人看的日记了。大概吧。我和我爸交流太少了。很多事全靠想象。
吃不完的鱼,他居然拿到金江大桥桥头去卖。江鱼奇贵,1990年代就贵到七八十元一斤了。我爸那一阵钓鱼卖钱,居然超过我妈妈的杂货店收入。估计就这事二老又要斗嘴了。
为保护生态,执法队见人卖江鱼是要没收罚款的,要卖最好去金江大桥桥头。金江大桥桥头挨近长途班车站和火车站,南来北往,鱼龙混杂,是个灰色区域,穿制服的人一般不会单身前往。
“桥头上混的”,是有点凶险的专用语。他在电话里有几次居然自称“桥头上混的”,还说自己身着蓑衣篾帽旱烟杆全套。
蓑衣用南方常见的棕榈树网状纤维一片一片织成,看起来处处空洞,却不粘雨。篾帽直径约有一米三四,用慈竹皮编成两层,中间夹块油布,往头上一戴,就是古龙的“大侠”模样。
在我的想象中,我爸披着蓑衣,戴着篾帽,看不见脸,就让人看见从篾帽下沿伸出的铜亮旱烟杆。(他抽起了当地人的旱烟杆,肯定是为了配合蓑衣篾帽)。我觉得他这副模样不全为卖鱼,也为唬我一跳,冷不防把我抓住,大叫:“我是你爹!”——我十五六岁时和他分歧巨大,常离家出走,破罐破摔就跑到金江桥头操社会。心想这里就是我爸最不愿意来的地方,我偏要来。
这里有地痞、小偷、婊子、骗子,当然还有私售江鱼的渔夫。那个时候我真不可能想到他会化妆成一个渔夫站在那里。
有一天,我爸打来电话问我。
你六岁时,我带你进城看国庆烟火。咱们两爷子在渡口桥看到一条鲶鱼,四百多斤。这事记得否?我说,四百多斤!那可真大。不过我完全记不得有这事。记性还不如我么,我爸大为失望,还说让你帮我回忆回忆,把事情弄明白呢。我说爸,真没印象,太小了吧。胡说,他说,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六岁正是记忆力爆发性增强的时候。你再想想,我给人打了包票搞明白,说我家有个现场记录器,就是你呢,别让我下不来台。我问,跟谁打啥包票啊。他说,刀医生啊。哦,我知道了,原来是两个退休老头吹牛聊天,我没放在心里。
那天我下班刚回家,我爸电话又来了。想起来没有?老爸你先说说你记得的事,看看能不能让我也想起来。于是我一边吃饭一边听他讲,叙述的内容远远超过记忆,往往如此。
据说,一九七七年国庆,咱们两爷子从九道沟走路到红格,再从红格赶车到市里,打算在文教局招待所歇一晚,看了国庆烟火再回。后来才知道因为毛主席才逝世一年,咱们没好意思放烟火。咱们两爷子看不到烟火,就在金江大桥闲逛,见有人用板板车拖了比猪还大的一条鲶鱼在街上卖。
鱼大得像神物,没人敢买。卖鱼变成了展览。天气热,鱼很快就坏了。卖鱼的只得再拖着板板车,将臭鱼倾倒回江里。
卖鱼的倒霉透了,是倮倮寨的一个小伙子。展览时还很得意,很受观众吹捧,鱼一发臭,观众就改口,骂了他个狗血淋头。说他必受诅咒。果然,再后来他就被人举报,说他大鱼不交公,私自投机倒把,被严打了。背井离乡,出门避难去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离开户口所在地,想想他会有多惨。
听完他的故事,我得出结论:他在写小说。而且还是那个小说。
有一天,他和钓友刀医生在洄水荡钓鱼。
刀医生是我出生地九道沟的亲戚,我开裆裤朋友小五斤(刀牧)的爹。小五斤的事和刀医生,也许我已经在九道沟的故事讲过不少他们的事了,这里单说刀医生和我爸一起钓鱼的事。
刀医生从九道沟卫生站退休后,到小五斤开在金江大桥桥头的旅社帮忙,也就是养老啦。在桥头遇到我爸卖鱼的,对我爸从一文弱书生华丽转身成“桥头混的”大为吃惊。两老头一个惊讶一个得意,立刻凑在一起。烧了一条江鲢,聊了一下午。随后刀医生也购置钓具,蓑衣篾帽,随我爸去洄水荡钓鱼。
知道有刀医生和我爸一块后,我松了一口气。有伴儿就好了。毕竟一个孤老头,在穷山恶水最荒芜之处钓鱼,是真的我爸,并非在欣赏一副独钓寒江雪的古画。
他们正在钓鱼呢。横江过来一条小船,似乎是冲着他们来的。确实,小船慢慢划到他们跟前。你们在这里钓鱼啊!划船的人说。对啊我爸说。那人稳住船,半天,愣愣看着我爸和刀医生。你们不是本地人,他得出结论。
咋说我们不是本地人,刀医生开口辩道,我九道沟呢,金江桥头开旅社,咋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不会来洄水荡钓鱼,那人说。
咋呢?我爸问,这里鱼又肥又大。
当然又肥又大,这人说,吃死人的。
我爸在此钓了有些次数了,确实没见有别人来此钓鱼。还以为这里是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钓鱼点。殊不知洄水荡在本地是大大的有名。
这里我插一注解:横断山区,山高水恶,十里不同天。没公路铁路之时,看起来就在江对面的人家,公鸡打鸣都能听到,真要走访,没准得化两三天时间。所以这里遇到一个本地人口中的本地,指的正式他立着的地方,划一下范围大概就同一条山沟沟百十来户人家之所在。
本地人从不来这洄水荡钓鱼,只会到这里打捞尸体。上游淹死的人,多会流到此处集中,本地渔民便把尸体捞起来等人认领,每具尸体八百元。那二年,八百元可是巨款,本地人也因此业闻名。说了半天,这个闻名的本地其实就是金江村,人家大概就在附近某匹山脚。我爸一门心想在大自然中钓鱼,存身于超然境界里,不知金江村就在旁边,也不知道金江村闻名的捞尸业务地就是自己天天钓鱼的洄水荡,还不知道自己被村里人议论过一阵了。
上游有死者确信是掉江里了,也会传讯给金江村准备来洄水荡打捞。还根据落水时间,江水流速,说出几月几日会到洄水荡,本地人按时划船到洄水荡打捞。
这个本地人就是接报来此打捞尸体的,阿索拉县有位女的文化人投江自杀了。是个文化人,他说,没文化的不会自杀。
金江村人胡说八道,我爸说。不过,九道沟乡属阿索拉县,我爸在九道沟中学教书二十多年后才被调到市级中学,阿索拉县文教系统,我爸认识不少人。刀医生提议我爸给阿索拉县的熟人打电话问问看,说不定能问出是哪一个女子自杀了。我爸拿不定主意。我们不是来钓鱼的嘛,打这个电话来干嘛?刀医生额了一声,说都晓得鱼吃死人吃肥的,你还敢钓啊。
说得也是,眼前那个金江村的捞尸者,正在撒网呢。撒一网,收起来看,没有,换一处,很仔细地搜寻整个洄水荡。
他们收了钓竿,看那人打捞。肚子饿了,吃饭团、牛肉干、花生米,喝老白干,继续看。那人捞了一圈,收起网,高声朝他们喊,收工咯老俵,明天又来。
我爸回了家,没忍住,给阿索拉县城文教局熟人打了电话。搞清楚了,阿索拉文化馆的罗馆长自杀了,是个彝族美女,年轻时是跳啰嗦舞的台柱子。啰嗦舞应该都知道吧,能歌善舞的彝族人最著名的舞蹈,凉山州对外宣传的保留节目。当年周恩来搞外交,常带啰嗦舞表演团出国。于是呢,从凉山州到楚雄州,彝族影响之区域,每个县,每个区,有文化馆的都在练啰嗦舞。攀枝花市夹在凉山楚雄两大彝区中间,有一个因善跳啰嗦舞的彝族女孩逐渐成长为县文化馆馆长,我们一点都不奇怪。
我爸将情况讲给刀医生听后,次日两人又来洄水荡看金江村人打捞。又白等了一天。不过回到家,阿索拉县的熟人朝我家打来电话,说老赖,罗馆长的女儿想和你说点事。然后对面电话换了人,一个女孩,说自己叫阿朵,罗馆长是我妈妈,然后就泣不成声。
(饿了,没法写了。改天再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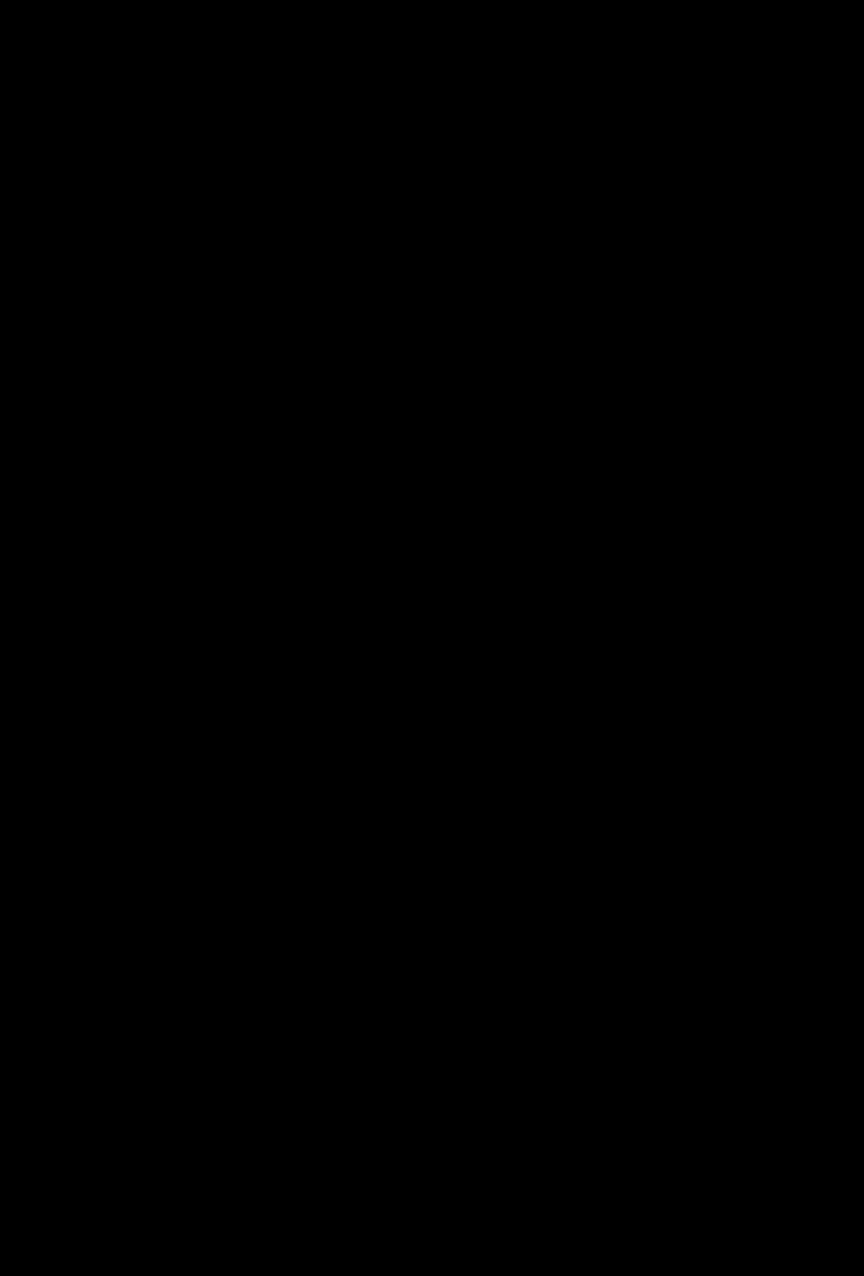
感觉有一千条故事线,我自己都看糊涂了
刀是好姓,是傣族吗?
傣族刀姓比较多,不过我认识的这家是哈尼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