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地方(暂)部分
黄葛树
小五斤从公社那边跑来找我。快点,你爸过河了。(在我的记忆中,小五斤就是这样登场的)。我们冲下万年坡,跑到黄葛树,爬上树,在枝叶间藏好,目不转睛盯着大田,然后,毫无意外,我们听到很多说话声。
黑莽子是我们家的啊,这是小郑官的声音。
黑莽子是一头大盘角的黑水牛,见穿红裤的女人就追。黑莽子属于小郑官家是解放前的事了。他爹生前就爱说,黑莽子是我们家的啊。他爹死后,留给他这句话,让他接着说。这句话也会由小郑官传给他儿子,如果他娶得到媳妇的话。我听着(或许是想着)小郑官说这句话时,会看见黑莽子和别的动物低头往溪里舔水。
别让牲畜吃到池里去,池子是人喝的。还会听到有人这样说。
池子就是一些青石围起的泉眼处。树荫中的水是透明的。不过水仍有自己的明暗,彼此扰动。扰动时水里的东西会变形。沙、石头、黄葛树的老板根、时隐时现的小鱼,变大变小。泉水都来自居那若罗。那是一座神山,也是一个隐藏的海,没人看得见。风水大师站在泉眼边用罗盘的指示,往远处的山峦看看,有时会讲出一些秘密来。这些秘密便和居那若罗有关。
也有声音问王田义那块田的事。我们都知道那块田是咋回事。很多年了,就在大田尽头。被大田挡住了,降低到河里。这里看不到。每年冬季,王田义都要带他三个娃儿分与水争地,用石头从河里砌出一块田种谷子。年年砌,年年被水冲。有时候没冲走全部,能收来半箩筐一箩筐谷子。最多一箩筐。公社时,人的劳动都属于集体,王田义抱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干私活,干部们要批斗他。但他出身贫农,不识字,不说话,一身蛮劲又不怕打。商量来商量去,干部们想不出怎么批斗他,就将他的工分由全劳力按半劳力算。包产到户政策下来后,工分制废了,大家都可以开心干私活了。王田义倒成了改革先锋。我爸和肖老师是这样说的。以历史眼光看,是这样的。这话知识分子腔调,进不到王田义的耳朵里。再以后,王田义死了,他多个魂魄中的某一个,附在黄葛树的一片叶子上。那样也许他才会听到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会对他讲讲这话到意思。当然,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人有三魂六魄,也说有更多。生是魂魄的聚成,死则是魂魄的散离。散离的魂魄何处去?横断山这么大,这么多东西。草木、禽兽,水和石头,没问题的。黄葛树村的黄葛树比村落古老,比村落古老的东西对茫然散离的魂魄特别有吸引力。每年春天到秋天,黄葛树百万计的叶子,,每一片都能传递九道沟或者更大地方的魂魄说话声,絮絮叨叨。这就是我能在黄葛树枝叶间听到很多很多消息的原因。树里有,树下也有。晚饭后树下总会坐一群人闲聊。活人的声音和魂魄的絮语混在一起,分不太清楚。黄葛树七八个人合抱不住那么大,树上有很多叉叉窝窝的,让无数喜鹊筑巢,让我和小五斤这样的小孩舒舒服服地趴着或蜷着。太舒服了有时会睡着,有时会醒着,或者半睡半醒的,也分不清楚。现在看来,我在黄葛树上的时光,是感觉和想象混合,真实和虚幻没有区别的时光。很像我正在写作的时候的状态。不过现在我已失去了小而敏捷,柔而适应多种空间的儿时身体了。很多感觉是从回忆来的而非直接的描述,我的语言就像你现在读到的这样,已缺乏让你要认真对待儿时记忆了的说服力了。乔乔,你还在听吗?
我记得的是:今天树下的人下注了十个鸡蛋,赌王田义的田会不会被水冲走。夏天已经到了。
原来已是夏天了,大田的水稻已抽穗。如果大人走在田埂上,会露出腰以上的部分。小孩则只能在蹦跳时才看得见他们脑袋。大田是有十三亩的一整块田。在九道沟,这么大一块田是个奇迹。大田给我们带来那个方向辽阔的视线,看得见河对岸的公社,看得见河下游准备修宝塔河口以及更后面的碧隐峡。很舒服。
便有一个穿干部服的“我爸”, 身影出现在水稻上方。正慢吞吞地,越来越近了。这时候小五斤突然说:“你爸。”我被惊醒了。
似乎是同一个地点的另一个记忆(分不清楚中间有没有间隔,比如其实隔着其他的事我忘了讲):我和我爸,黄葛树下,等我妈回来。同时也有另外三人蹲在树下,目不转睛地看西面的白泥巴垭口。
白泥巴垭口在任何时候都很显眼,此时跑下羊群,在夕阳里弄得烟尘滚滚。太阳最终落了下去,把一些云烧起来。大片的火烧云光芒万丈,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随后变成深灰色。
看火烧云烧过,幽暗中,那经常聚在树下聊天的几个人,王田义、小郑官、王虔贵、老野狗,发现了我爸,便一个接一个起身,再弯腰喊,老师。我爸则一一礼貌作答。
我爸刚从劳改农场回来,村里人有些敬畏。他们过于夸张的恭敬,让我爸不知说啥话好。还是小郑官机灵,将手里烟锅递给我爸。我爸说,戒了。小郑官退后一步,蹲下,其他几人也随他蹲下。
小郑官对另几位说,烟都改得掉,太凶了。我爸闻言对他笑了笑。因此小郑官再次站起来,递出烟锅,抽一锅嘛。我爸还摇头,小郑官再次说,连烟都改得掉,厉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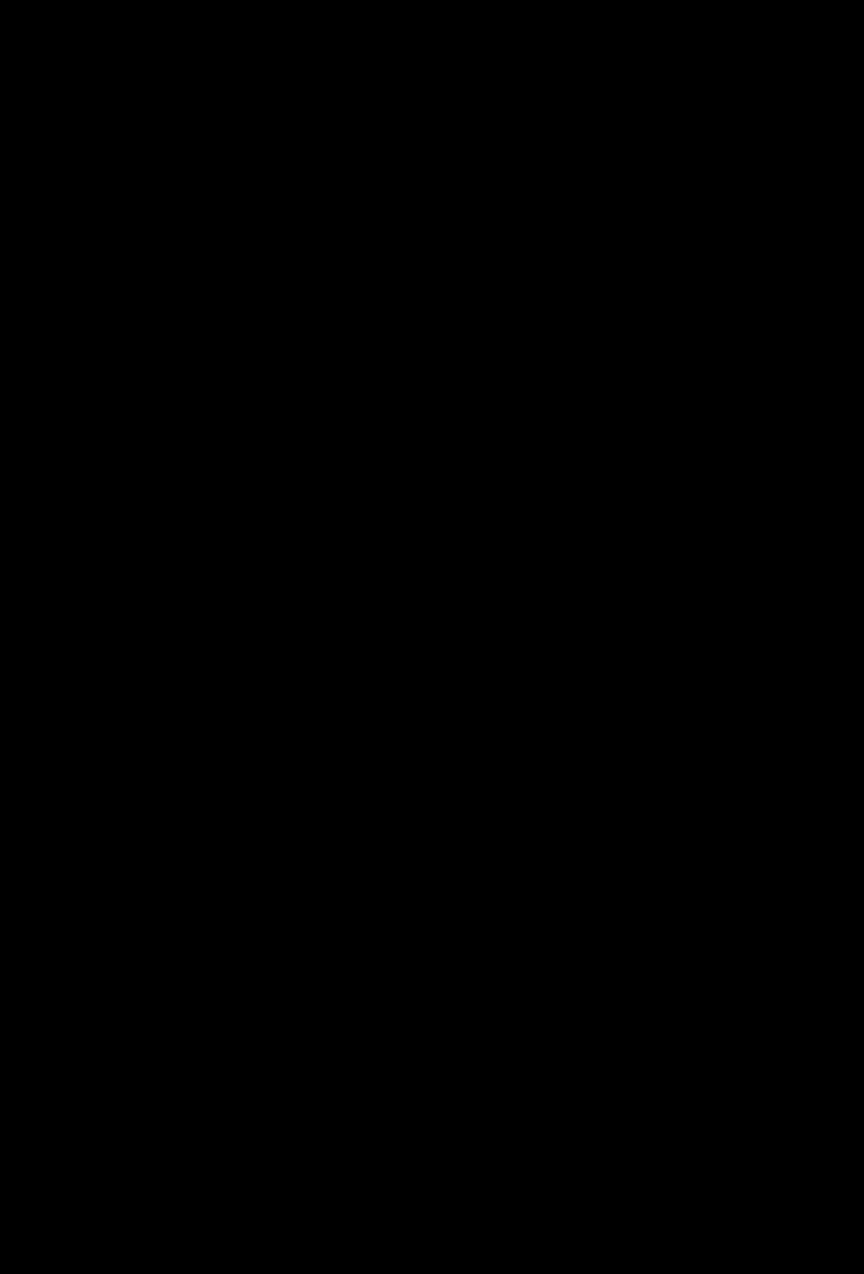
伙伴
娃娃生下来都要过秤,让妈妈知道少了多少肉。小五斤生下来时只有五斤,我生下来有八斤四两。八斤四两超重婴儿,我在小五斤面前特别牛。小五斤的爹,医疗站刀必显刀医生,傣族,十多岁时在鹿县我外公的回春堂当学徒。我四岁那年,外婆被斗争打成重伤,小五斤他爹敢登我们禾家门来帮我外婆疗伤,是个记恩讲义气的人。他刀家与禾家本有亲戚关系,属于表亲,小五斤他爹应叫我妈妈表婶。但他又娶了高堰沟马家马雪萍,高堰沟马家则出自我外婆马仪方鹿县城马家旁支。幺房出老辈还是咋的,从马雪萍那边算,辈分上我妈整整比马雪萍高三辈。虽然马雪萍岁数比我妈妈还大,却要叫我妈妈表祖宗奶奶啥的。大人之间,搞点笑,也能搞清楚,到小五斤和我这里就完全不知怎么办了。小五斤担着此心事,常主动提出和我打商量。咱要商量啊,咱到底该依哪一方叫呢。是依我爹这边呢,还是依我妈这边?我觉得都行,反正依哪一方都是咱们辈分高。但小五斤第二个疑问就太乱人脑子了,他说,依我爹这边我该叫你表叔,依我妈这边我应该叫你老祖宗,都不科学。因为我是我爹和我妈一起生的得嘛,两种亲戚我都该占,一边占一半。所以我在琢磨,你也要帮我算,因为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哦。表叔加老祖宗除以二,该咋叫呢?不晓得,我们一辈子都理不清楚这件事。
有一天,我和小五斤要一起到石门坎看火车。到石门坎需要吃过早饭便就开始走,所以吃过早饭,我就为我和小五斤捏了两个很大的饭团。捏饭团时妈妈没在意,可是当我拿水壶来装水的时候,妈妈还是没在意。我说,妈,我要和小五斤去看火车。妈妈随口说,别跑远了。看火车多大的事啊,要看火车还能不跑远!算了。小五斤来后,他认为我的水壶带子太长,于是在带子上打了一个结让它变短。这是布带和锡壶都染作草绿色的军用水壶,出远门须背着。水壶上写着笔划潦草的五个红字:为人民服务。我们往坡上走。这个冬天的早晨,除了我们两个小孩,还没有谁在这个时候出门走动吧。太阳不晓得出来没有,从东方山峦后涌起兰白色光芒雾,到处都是透明雾状物。我们来装鬼吧。好的。于是我们用力直着上身,平直伸出胳膊,两脚碎小而急促地跑动。跑到万年坡坡顶,我们有些莫名其妙地站了好一阵,才看见我妈妈扛着锄头出门,往团结水库那边走去。接下来,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条青竹镖。这种青色的蛇,通常待在沟底林木深处,青油油发亮。太阳出来的时候,它跑到坡顶阳光里来发亮,亮得变成灰色。我和小五斤停下来等它过去,但它昂着头,熟练地沿人走的路往前游,好像它也要到石门坎一样。后来,在凉风坪,青竹镖转入一条岔路,我们差点跟着它走。跟着去了就完了,小五斤一本正经地说。当然,肯定完了。我们还遇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火箭草、铁线草、灰灰菜、月母草、何首乌、地瓜藤、明油枝、山楂树、云南松、马尾松、衫树、青杠木、冬青树、栎树、莎老树、杜鹃花、山茶花、报春花、攀枝花、火焰花、打烂碗花花、万年坡、冷水箐、河尾子、凉风坪、禾家堡、黄泥巴垭口、白泥巴垭口、奶头山、王麻子洞、温泉、癞子洞、倮倮寨、太阳沟、观音沟、将军岩、小黑箐、黑松林、石门坎。石门坎到了。如果孩子村里往我们这边看,应该就是龙周山十三峰从座往右数第六个的缺口处。真高,天空完全晴朗了。看得见五十公里远处的金沙江。我们看见了金沙江。金沙江边上就有火车,我们往那里看了一下午。
有一天,小五斤和我砍下小臂粗的枣树枝,削掉皮,放火上烤。烧火也很好完。在野地里找架起干木头烧成篝火,用偷来的火柴。钻木取火也试过,不过这个技术太古老了,我们太小搞不成。枣树枝烤一烤,压一压。反复压弯。一次又一次,直到它冷却后固定成为弓状。再把它一端系上最结实的牛皮条,牛皮条也是偷的。这可不容易。如果不是小五斤从生产队库房偷到牛皮条,我们不会想做一把弓的。系上牛皮条的这端,抵在石头上,另一端顶在肚子上,用力压得更弯,两个人赶紧动手,把牛皮条和弓的另一端系死。一把弓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干竹筒砍成竹条条。将竹条条一头削尖,另一头破开一截,插入公鸡尾翎再绑紧。弓和箭都有了。拿着弓箭,我们来到观音沟。沟里静悄悄的,应该没有其他人,可是我们就是觉得有人。小五斤让我爬在一块石头下面,自己取下弓箭,做好发射的姿势。只见他左手持弓,拇指微微翘起,右手把箭前端放在左手微翘的拇指上。箭尾抵在弦上,两手用力把弓拉开。他瞄准的是一棵黄葛树的枝叉中间,他觉得那里会有什么东西冒出来。三四分钟后,他对我说,不要动,随后他换了一个动作。还是保持着随时发射的姿势,只是手上没怎么用力,腿却轻轻移动。快到那棵黄葛树跟前时,突然跳到树的侧面,拉开弓对准树的另一面。他就这样一棵树一棵树地搜寻着。观音沟里静悄悄的,稀少的阳光落下来,漂在眼睛上或者溪水上。等他把五十七棵黄葛树都巡查过了,就用普通话大声对我说,一切正常。然后换我来,我也让他爬在一块石头后面,保持警惕。然后把干过的事重复了一遍。刚刚合适的有一天。玩完了就回家吃夜饭。
有一天,小五斤叫我去供销社看稀奇。来了城里人,要当九道沟人,稀奇不稀奇?在供销社院门外咱们看见阿黄。 一个微胖,白得像富强粉馒头的男孩。一看就不对劲儿。他对我们咧着嘴笑,张开一只手掌。手掌中间有两颗因久握而变软的大白兔奶糖。我和小五斤毫不犹豫取过奶糖吃了起来。吃了他的奶糖,我们叫他带我们去他家看看。他有点傻乎乎的,说好。他外地口音很重,后来有电视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说的是电视机里的那种普通话。
阿黄妈妈叫叶紫,一个皮肤白,动作小心翼翼但身段很直的四十多岁妇女。阿黄的姐姐,也皮肤白,胸脯好大。
小五斤看清这家人的情况,就盘算如何美美地揍阿黄一次。他说阿黄长成那样,揍起来手感好,可长期揍着玩。小五斤就这习惯,搞不清楚他要表达的是欺负人,还要让人对他印象深刻。阿黄跟妈妈姐姐来九道沟,转学和咱们同班,小五斤要揍他有的是机会。但当他有一天见我吃着奶糖,单独和阿黄呆在一边说事时,不禁大为吃惊,不得不和拉我到一边商量。
在他看来,阿黄有四大污点。一胆小怕事,二脸太白,三有外地腔调,四是姐姐胸脯太大,必须挨揍。但我不准他欺负阿黄。我耍的就是老辈子的威风了,小五斤只得认账。说你是我高三辈的老辈子,我卖你的面子,但阿黄要记恩。为顾全大局,我带小五斤找阿黄商量,建议他要记小五斤的恩。小五斤不打他便是对他有恩,这便是九道沟对落单外地人的逻辑。咱们都知道,这可不仅仅是小朋友不讲道理。小五斤不提他不敢违背我这个老辈子的意志事,将自己所受压力全算阿黄头上,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仅限于九道沟才流行的逻辑。阿黄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他胆小怕事,一般来说不过分的要求都会答应。过分要求,他不能答应,会拿出大白兔奶糖行贿,让对方放过他。大多时候能解决问题,但遇到喜欢趁胜追穷寇的,反而更狠,说他的水果糖是他妈妈贪污国家财产的来的。遇到这种人,他真没办法。好在他和我小五斤结成死党,遇到这种人我们会撑腰。他答应记恩,真心实意的,小五斤却不因此改变对阿黄的看法。但他得听我的,三人要结党。那一阵我忽然产生了三个人才能形成团体的信念,固执得很。要称之为团体的,必须到三个人,我说得斩钉截铁。小五斤无可奈何。总之,三个小伙伴聚在一起,事儿便多了。
八路军埋伏在一个日本鬼子本来不去的地方,要王二小带日本去找,三个人,这件事可以演了。王二小,八路军,日本人,刚好三个。每演一遍,便讲一遍这个故事。还有周扒皮的故事。周扒皮半夜学鸡叫。我们便想找到九道沟最先打鸣那只公鸡,为此专门去我家住过一宿。因为我家在万年坡,地势最高,夜里能听最远。当然也没找到,因为睡过时间了。诸如此类,特别忙。不过有一阵,我和小五斤同时对阿黄很不满。起因是阿黄说他是渡口市人,不是鹿县城人。还振振有词,说他们一家是从上海援建渡口市过来的,是钢铁公司的人。钢铁公司知道吧,我和小五斤完全不知道。于是他露出些许看不起人的意思。这已经有点让我上火了,最让我生气的是他说九道沟划归渡口市而不属于鹿县城咯。我才不干呢。我表现得像个恶霸,命令小五斤揍他。阿黄惊呆了,回过神来撒腿便跑。边跑边求饶,我认输,我认输,我也是鹿县城人。确实,没人告诉我们。早在一九七八年,九道沟就被从鹿县城划给渡口市了。这事干得像阴谋,背着咱们做的。我是在一九八六年以后才承认自己是渡口市人的。那时我考上了渡口市师范学校,对林小梅回忆着九道沟的往事,无论是时间和空间,确确实实地呆在渡口市里了。而九道沟里面还有很多人,一九九五年前都还以为自己是鹿县城人。一九九五年后,渡口钢铁公司启动了位于九道沟境内的储量高达三十亿吨的钒钛磁铁矿开采,将整个九道沟彻底变成一个工矿区,才算让他们从梦中醒来。
至于小五斤,永远不会尊重事实。既不尊重时间,也不尊重地点,大概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渡口人。
写的真好
等一个鹿县城过来的朋友
公路刚修通没多久的事:我,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站在街中心,抱着胳膊,等一个鹿县城过来的朋友。
阿黄从供销社出来,脸上晃着汗,一见我便眯着眼小跑过来,和我并肩站一处。站了一阵,他问我:“我们干啥啊?”
我说:“等一个鹿县过来的朋友。”
他精神为之一振,站得笔直。
随后来了小五斤。他谨慎地慢慢走来。“你们干啥啊?”
阿黄说,“我们在等鹿县城过来的朋友。”
“牛逼,”小五斤说。不他并未过来和我们站在一块儿。而是去到电影场入口两排铁栏杆中间,选了一根栏杆翻上去坐着。
他脑袋就挨着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今日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他用袖口擦掉那排字。“今晚不放瓦尔特了,咱们想看啥?”
我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就是最好的,没有更好的了。
“肯定有,”小五斤说,“肯定有比瓦尔特更好看的电影。”
于是我不想理他了。稍后,他嬉皮笑脸地问,“你鹿县城的朋友啥时候到啊?”
“快了,”我说。
“我打赌,我一根烟抽完你鹿县城朋友也到不了。”他从兜掏出一根烟,点燃抽了起来。“要不要过来抽一口啊,阿黄。”他嘻皮笑脸,冲着阿黄。阿黄涨红了脸,不说话。
“阿黄!”小五斤跳下栏杆。小五斤又想打阿黄了。咱们一块玩都三年多了,小五斤始终未能丢掉这念头。他为压制想打阿黄的冲动,经常搞得面红耳赤。
我移到到阿黄前面,还是像之前那样两手抱胸而立。小五斤不再往前走。他摇头晃脑半天,转身在小黑板上“今日电影”下面,写下“等一个鹿县城过来的朋友”。
确实,这也可以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嘛。小五斤还真是天才。
一个多月前,九道沟到夕格达段的公路正式修通,能直通到区市了。一辆披红挂彩的班车从市里开来,停在供销社门口。下来一些干部,把我们这些学生带去班车面前排队,听区上的领导讲了一番话。之后,班车便两天一趟,一天走在来的路上,一天走在去的路上,中间在供销社停一夜。极少见九道沟人上车,来来去取都是钢铁公司下乡来采购的人。阿黄十分活跃,就像见到亲戚一般。没两趟老乡们也搞明白了,便带着蔬菜鸡鸭等班车。然后就有消息说,市场要搬到这里来了。
市场?就是买卖东西的地方。我们有市场的,九场,也叫老街子。我九舅公家在老街子铺面最大。每周一次赶集,成交最大的是彝族人赶着马下山来的以物易物。土豆换大米,五斤土豆换一斤大米。不过他们最稀罕的是针,一根针可以换他们十斤土豆。他们还拿土豆还换酒喝,晚上的老街子,总有喝醉酒彝族人留下了,迷茫地游荡着。几乎没见过彝族人来供销社。大概是供销社不提供以物易物,而且供销社的东西对彝族人也没啥必要。老街子的市场搬到供销社这边了,彝族人怎么办呢?我努力地想。
此时,这个重要时刻中的一个点。我站在街中心,抱着胳膊,等一个鹿县城过来的朋友,将重要性完全找到了。
到晚上,我躺床上,使劲儿想着。想啊,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有一个鹿县城朋友的人。
鹿县城来的朋友来了,大大咧咧冲我说,喂,朋友。一般人会因此吓一跳,胆小会慌忙跑开。比如阿黄吧,准会撒腿跑回家找他妈妈。他妈妈则会费力地从棉袄深处掏出十字架让他亲一下。
基督教没啥用,鹿县城过来的朋友才管用。朋友。或许有一天,我会把小五斤从亲戚关系升级为朋友关系。阿黄呢,得先升级为亲戚关系。但是现在,我需要一个从鹿县城过来的朋友。
没啥事,我对他说,就是该见见了。这就是鹿县城过来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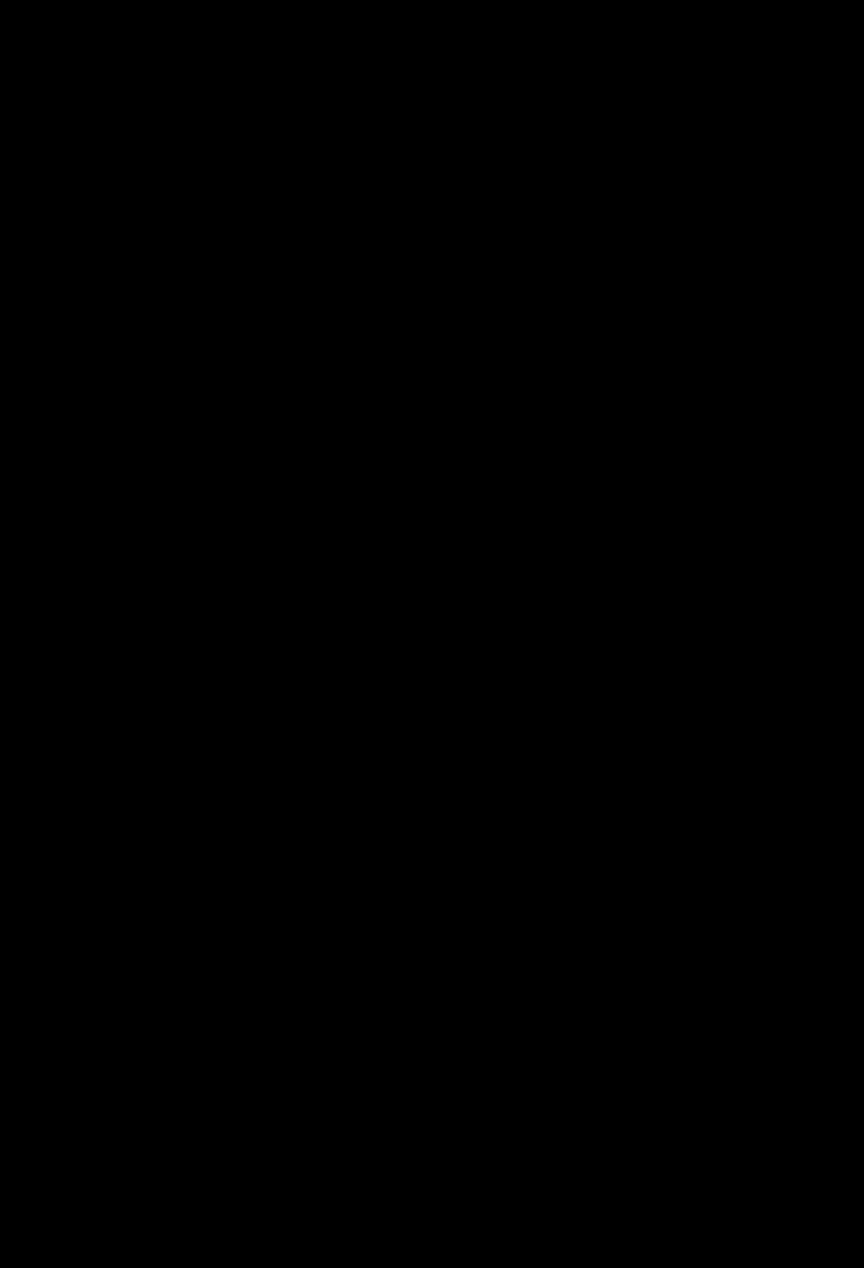
从九道沟村到市里的班车两天一趟,早上七点半在供销社院里上车,下午四点过到市里。
中途到红格镇时,班车停下来让人吃饭,我们没有吃,想省到市吃,现在觉得饿极了。
我们东张西望,馆子到是看见了两个,可不敢进。我们希望找到油布支在墙角,胖胖的老板娘坐在下面扇着蜂窝煤炉子煮面条那种。
我、小五斤、阿黄,为进城专门新洗了书包,穿着新衣服,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少年。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便不停地走动,只要一被人看,就赶紧溜开。
我饿了,我说。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小五斤说。
我们摸着江岸上的水泥栏杆,边走边看。这就是江啊。很多小溪汇成河,很多条河汇成江。江上开着冒黑烟的船,突突突,太了不起了。更了不起的是横跨江峡的大铁桥。
我们跑上桥,扶住铁栏杆,小心地走。小五斤将脚背勾紧在栏杆下面的横杠上,使劲把上半身伸到桥外面。敢不敢!敢不敢!我不敢,不过我宣布了我三舅就是在这里游过金沙江的。
阿黄说,我也饿了,不过我们应该到我爸家吃饭。外面吃,怕不给咱们贵死。咱们赶紧去找新华书店,买了书还要找我爸家。在我爸家吃过晚饭正好看国庆焰火。我爸家住七楼,知道七楼有多高吗?不知道吧,马上就知道啦。全渡口市最好看焰火的地方。
新华书店,从桥头斜坡上去300米一个转弯处,对面是百货大楼。真热闹,再是靠边走也要被挤到人群里。很多人都提着火焰棒、鞭炮、瞿瞿花。阿黄大声说,我说得对吧?今天晚上肯定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小五斤被挤在另一边,大声回应。当然,国庆节嘛。
那时候的我们,多活跃啊,显得特别聪明。表情、动作、话语都栩栩如生。现在我敢确定,我第一次进城那年十二岁,进城是为看国庆烟火和买书。九道沟没书店,鹿县城倒是有,但没有国庆烟火,也没有阿黄爸爸家。我这也是第一次,与几百人挤在一起,还都是城里人。一些姑娘,皮肤白皙,穿着连衣裙。她们真的不一样。我甚至嗅到一个撒有香水的姑娘,听见她用很标准的普通说:“哎呀。”只有普通话才能说出后面那声“呀”,四川话和云南话都只能说出前面那个“哎”,最多把它拖长些,挽几个弯儿。
我挤在城里人中间,觉得他们友善。这和衣服整齐,过节,说普通话有关。还记得一些事,比如,阿黄和小五斤争了起来,大概是阿黄说,城里都是这样穿的,而小五斤显得愤怒,说你不会以为你们家是城里人吧。于是我想到了阿黄姐姐的乳房。四年级时有一晚我留宿阿黄家,梦见我撒尿去淋一个死人脑壳,当时就想,糟糕,我尿床了。醒来后果然如此。我不得不背对阿黄,用力弓腰,将他推远,在拎着被子角使劲扇风。直到凌晨才把床单弄干。
我不担心阿黄,我想的是阿黄的姐姐,羞愧得要命。哎呀,我想。我想的就是这个:哎后面有个呀。穿连衣裙的城里姑娘,人人都有大乳房。于是我红着脸朝小五斤喊,你不许欺负阿黄,人家爸爸住城里,当然是城里人!
我跟着那撒香水的姑娘,想再听她说普通话。可惜她只说了声“哎呀”,就进了百货大楼。小五斤和阿黄在书店门口喊我,阿华阿华,这边这边。
买了好多书。我买的是《初中数理化守则》,《动物的故事》,《四川地图册》,《云南地图册》,《文笔精华》,《中国神话丛集》,等等。满书包。阿黄本来没带多少钱,看到我买得过瘾,便要我借钱给他买,说等会儿到他爸爸家后拿钱还我。小五斤先只买了一本,一听说阿黄可以在他爸那里拿钱,就把剩下的钱又买了一本。出了书店,小五斤觉得不对,想回书店把书退了吧。说到底,他啥时候看过书嘛!买也白买。可盖了售书章的书怎么能退呢?小五斤你就硬着头皮读两本吧,哈哈。阿黄保证说没事的,到我爸家就好了。
阿黄爸爸家在弄弄坪,阿黄也没去过。上了班车,见大家都给两毛钱,我便掏了三个人的六毛钱給售票员。班车一站一站地停,人们只顾上车下车,也不说话,个个都心里有数的样子。阿黄看得担心,问售票员,阿姨,弄弄坪到了吗?售票员问,你们到弄弄坪哪里?这会儿就在弄弄坪。我们三人傻了。阿黄对售票员说,我们到我爸家,我爸爸家在弄弄坪。售票员愣住了,你爸爸家不就是你家吗?阿黄红着脸摇头。哦,售票员似乎懂了,说,小弟弟,弄弄坪大得很啊。
刚才说过,班车里本来几乎没人说话。这无人说话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城里人总是心中有数的,或又担心起来,以为车上出现了小偷。现在大家听出有个找不到爸爸家小孩,先是一齐看住阿黄身上,又细细打量我和小五斤。我完全受不了这种打量,一阵阵想发火。阿黄低声问身边的人,我爸姓周,周馨方。在钢厂当工作,叔叔阿姨有认识的吗?旁边两个人搭腔说,不认识。有一个还认认真真地说,我们这一车的人都在钢厂工作,不认识你爸爸周馨方。其他人大声笑了。那人没有笑,还一直看着阿黄,等他继续问。阿黄没敢再问。车又到站时,售票员说小弟弟赶紧下车吧,怕越坐越远了。
我们下了车,站牌写着新二村。前面二十米远处有一片楼房,全都是七层高,很新,我们从未见过,四面挑着阳台。不过班车上下来后,阿黄的想法完全变了。
我们爬上垒成金字塔状的水泥管最上坐着,看着下面的楼房以及更下面的江,听阿黄讲他的想法。他说,十年前,我们刚刚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五六年后,我们有了三四层的砖房,十年后,也就是今天,有这些钢筋水泥的七层楼。我爸住的应该是四五年前那种房子,超不过四层高,比较旧。因为我爸很正直,不会舔当官的勾子,这种新楼房不应该是他能住的,也不愿住。
我们站在水泥管上,按阿黄说法,挑中三个矮旧小区,一个一个地前去打听。记得有个小区快到门口时阿黄就激动起来,说肯定是,直接往门里冲。(假如,是他四岁时记忆浮现呢?是可以这样激动)。里面一共有五栋四层的房子,我们前去一栋一栋低看,绕着圈看楼上的窗户,走到单元入口瞅瞅,觉得不像,然后走开。这些楼房上写的是冷轧厂职工宿舍。你爸是冷轧厂的吗。是冷轧厂,也属于钢厂,钢厂大得很,有十万人,冷轧厂、焦糖厂,都是给钢厂配套的。这一说我们都觉茫然,而且,肚子饿得快走不动了。
我们吃了什么,记不得了。那时的我,心思一定不在吃饭上。不然我会记得的。我记得的是,感觉阿黄好可怜。
吃过饭我们三人身上一分钱都没了。没钱住店,也没钱买班车票回家。便又回去水泥管垒成金字塔地方,准备困了钻到管子里睡觉。不过现在,刚吃过饭,精神好,就坐在水泥管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半个渡口市。大概九点过,升起了国庆礼花。礼花下是大桥的黑影,黑影下是流光溢彩的江。
这是我们看过的最壮观的东西。我们兴奋起来,梭下水泥管,沿着马路跑跑跳跳。因为礼花很多啊,我们跑跳了好一阵。
后来我们睡在一处街心花园里。巡警发现了我们,检查我们的书包。书上都有章,不是偷的,警察说,好吧,你们继续睡。五年后我在市立师范学校念二年极,和女同学深夜约会,意外发现这里就是当年我和我的小伙伴的露宿之处。这里叫炳草岗转盘路,街心花园长满夹竹桃,叶子很青,阴影很重。我对林小梅说,警察走后,凌晨三点,我们决定走回九道沟。沿公路走九十公里,到新民时,小五斤找了条山路,应该走了七十多公里吧。
终于进入九道沟境内。那就不怕了。我们扯花生吃饱。在野猪沟水库,下水洗了个澡。我说水里有死人味儿,吓得小五斤差点被淹死。
阿黄姐姐的死
差不多就是清明节前后吧,在河尾子水库看见了桃花。
妈妈的缝纫店门口开张后,我们就不太回村子了。我坐在缝纫店门口,看门内投到路面上的光,还有的影子。
光非常明亮,夜游的小蚂蚁不小心爬入光里,慌得触须都不晓得往哪方摆了。清清楚楚的。我等着,看还有什么小东西要倒霉。或者我用两只手掌,十个指头,做出蛇的影子、狼的影子、乌龟的影子。这是电灯照亮一整块平地方才好玩的事。当然,我们有电灯了。我还记得那天傍晚,全村每家人都聚在电灯底下。等灯亮,再测试开关盒有没有用后,一起跑到黄葛树下,欢天喜地,相互汇报。我家电灯亮了,你家呢?我家也亮了。就这样。没人不高兴这事。电灯是个好东西。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还真难得呢。
发电用的水电站,是我三舅到猛粱坝做上门女婿后,带村人与彝族打了好几架才协商修成的。原因是要把水位太高,水流冲力大到带动涡轮才能发电。工程师设计的大坝要建到半山腰,在彝族人的势力范围。彝族人的山水是不让乱动的,三舅没到孟梁坝之前,和彝族人就交涉有些时间了,一直不成。三舅来后,两三次架打过,协商成功,修好水电站。不是说彝族人怕我三舅,而是我三舅了解彝族人。协商包括打架,打架也是协商,这是彝族方式。彝族人敬重英雄,重要的事,非打架不足以显示重要性。
咱们有电灯又有公路了。公路也是没人说坏话的东西。我家缝纫店门口出来的光,就照在九道沟新修,才和市里连接的公路上。以前有条旧路,通到鹿县,马帮适用,吉普车也很难走通。我记得我四岁时,一家人运送装在棺木中的外婆走过老路。可是大家都认为是我的想象。外婆和外公埋在一起啊,在奶头山,别胡说八道。大人说。围绕这件事还有很多事,可是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我忍不住会做梦,可我已经不想说了。
公路修通后,市里来的班车隔天来一辆。停在电影场门口下客,开到供销社院里过夜。次日又开到电影场门口上客。电影场门口十字形路口附近,很快就有了商业。沈天棒的台球摊是第一个,我们家的缝纫店紧随其后。再接着,乡政府将一周一次的市场从老街子搬来此处。白天便能看见十个多老乡,愁眉苦脸蹲靠着学校围墙,一连串地摆出十多个地摊。鸡鸭蛋菜之类。除了班车运来钢铁公司的人下乡采购,没啥顾客。鸡鸭蛋可以拎回家下次再来,烂菜叶子就扔在摊子处。五六个烂菜堆子,臭烘烘的。全乡投机倒把的老油条都来了,要抓的话一锅端。有一次罗部长从头巡到尾,折回我家缝纫店,跟我爸说。我爸便国际国内给他上了一课,说风向变了。投机倒把这个词语可能也要过时了。
沈天棒的台球摊子,就在我家缝纫店对面,医疗站门口的坝坝里,搭着阳棚,棚下吊着一百瓦的电灯。可能是九道沟最亮的一盏了。
听说段天棒台球赚了不少,这阵在市里拉关系买录像机电视机,要增加录像放映。这是相当大的新闻了,我和小五斤都眼巴巴地盼着呢。录像是什么玩意呢?据说好看极了,比电影场的电影好看一万倍。电影场就在我家缝纫店右边过去三十米的十字路口,我们在那儿看过《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上甘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不过我最喜欢的《未来世界》和《大西洋底来的人》,不是在电影场放的,是在106地质队放的。我问过放映员丁兴国,丁表叔啥时候放《大西洋底来的人》啊。他问啥?啥?完全不晓得有这部电影。连大西洋是啥都不晓得。想到这里,我倒是想去和小五斤聊聊看,如果段天棒的录像摊支起来了,会不会放《大西洋底来的人》。要不我们就给他支招,放《大西洋底来的人》和《未来世界》。
这会儿小五斤在台球摊上跟着几个大孩子混呢。他又没钱玩,想通过讨好大孩子让他玩两杆。我不喜欢他这样。
忽然小五斤他们跑了起来了,我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快,刘有才家要死人!小五斤说。
我们跟着前面的人跑。我们后面,也出现了跟着我们跑的人。右边坡上,麻柳村的,也有三四个人跳到路上,和我们一起跑。我还是第一次看上什么叫“消息不胫而走”。一秒钟以前我啥到不知道,小五斤突然跑来跟我说,我就跟着他跑。他和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吧,跟着前面的谁跑,可能是沈天棒的儿子沈小强。沈小强也一定有个人跟。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谁都不会独自跑去,要么跟着人跑,要么拉自己的伙计跟着自己跑。
我们这一批,小娃娃居多,十多个。跑过学校围墙,左转下坡,跑到乡政府门口,再右转沿梯田田埂跑。跑过三丘田,到刘有才家了。他家院子坐落坡下,挖了坡角平出地基,屋顶正好和我们所在的田埂一般高。隔田埂不过两三米,带着助跑都能跳上他家屋顶。这时周围已挤满了人,我和小五斤拼命挤到前面,见刘有才骑着屋脊,拿着啄火枪,面前摆着盏马灯。
一个很多星星的夜晚,刘有才家屋后坡坎梯田间站满了人,围观屋顶上的刘有才。刘有才大声说,老子今天死给你们看。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只要新来了人,便重说一遍。
不断有人来。全乡的人都会来。这一想我觉得真不得了。
刘有才你干啥子哦,下来好好说,院子里高声说话的原来是我爸。我有点得意地望了望小五斤。我俵老爷就是拽,小五斤说。刘有才高声说,没说的了,老子今晚死给你们看。应是又有人来,大家忙随他视线看去,见新来的是阿黄和他姐姐,以及阿黄很不喜欢的未来姐夫康上进。康上进举着火把,因此大家都看见了阿黄姐姐高高的胸脯,她觉羞死了。
刘有才说,赖老师,你别劝我,劝我没用,你问我婆娘老丈母她们干了些啥。我爸说好,我进屋问,你莫急,等我问清楚再说。其实他早就问过情况的,假装这么一下,是拖延时间想对策。乘着等我爸的这段时间,小五斤绕人背后去找阿黄,将阿黄带了过来。阿黄本来站在姐姐身边,感受到那些人看姐姐胸脯的目光,又生气又尴尬的,过来和死党站一起后,松了一口气。我爸出门来叉手在腰站在院坝中间,说刘有才别大度一些,你老丈母卖条猪你就要自杀,值吗!于是有人哄笑了。刘有才分辨道,是种猪,九道沟最牛逼的种猪。我爸说,种猪也值不了几个钱,你一条命多少钱!把火枪扔了下来说话。刘有才说,你们莫不是以为老子不敢死吧赖老师。他倒过枪,枪口抵住胸口,使劲伸直一只脚,想用脚趾头扣扳机。弄了好几次,才让那个脚趾头伸入扳机眼儿。大家顿时紧张了,我爸放软口气。刘有才你真别乱来,你为一头种猪去死,死了也是个笑话,何况你不一定死得了,受活罪才惨呢。哈,刘有才说,我装的铅弹,野猪都杀得死。赖老师你以为我装的铁砂子啊。他放下枪,从袋拿出一枚铅弹说,瞧见没有,铅弹,不是铁砂子。康上进,火把照过来点,让大家瞧清楚。康上进真够傻的,还真将火把朝他伸了伸。我爸说,就算铅弹,也不一定打得死人哦。人没那么容易打死的啊。你问问小和平,他跟越南人打仗,伤兵比死人多得多吧,就是因为人不容易死。你没有杀人技术,十之八九把自己弄残废,死不死,活不活,到时看你咋过。刘有才没马上接嘴,过了一会儿再次倒转火枪,只是这次却将火枪枪口捅入自己嘴巴。示范了这个动作,他拔出枪问,这样会不会死人啊赖老师?我爸叹了气说,你等我想一下再回答你。刘有才得意道,连赖老师都被我考住了,赖老师你慢慢想。
小五斤不晓得发了啥神经,突然大声说,刘有才!你狗日的要死就赶紧死,莫吹牛皮不敢动真章,耽误老子瞌睡。可能就因为这句话,他后来挨刀医生暴打好几次。因为可能因为这句话,刘有才站起身,举着火枪对咱们这边扫瞄。反应神速的人立刻就趴下了,反应慢的人随后才趴下,胆小的人,比如阿黄,吓得一动不敢动,只觉两个膝盖抖得厉害,不听指挥。不过刘有才并未开枪,而是说,要死的是老子,轮不到你们这些看热闹的人牛逼。于是大家放心了,趴下去的人赶紧站了起来。
不过,咱们很多年后也没想通为什么刘有才会言而无信,当大家放下心后,他竟动作迅速地朝阿黄姐姐胸脯开了一枪。阿黄姐姐砰然倒地,两腿乱踢,嘴里噗噗往外吐白沫。
刀医生剪开她胸前衣服,两个乳房中间,现出一个拇指那么大的洞。洞口噗噗地响,溅出粉红泡沫,变成蝴蝶飞走。她后背还有一个更大的洞,流出的血更多,染红半个土坎,很多人的鞋子都粘上了血。我爸没说对,人是很容易死的。阿黄的姐姐,就这样死了。
(乡村童年故事,暂时小结)
我不晓得按亲戚关系该如何称呼刀医生,每次该喊他时都支支吾吾的。似乎终于有一天,我清清楚楚地喊了他一声刀医生,以后就按这样喊了,他也习惯了。
小五斤失踪两天后第三天中午,刀医生来我家要我想想小五斤会躲哪儿了?我说了三个地方,观音沟、团结水库、三倒拐,刀医生急急忙忙按我说的地点找去了。晚饭后我去小五斤家打听,刀医生说还没找到。我又想了一些地方,具体到黄葛树上的大树叉、观音沟后面一线天洞窟、三倒拐第二个拐弯处大和尚石和小和尚石之间的缝隙、冷水沁沟底下狐狸洞等等,十多个我和小五斤去过的地方,刀医生听得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找了。
我也觉得他没法找,这些地方只有小孩才找得到,才呆得进去。只能我去找找看了。
从刀医生家出来,我忍不住往供销社走。我担心阿黄。也想开导开导他,小五斤被刀医生打得离家出走,能不能别怨小五斤了。小五斤是闯了祸,那是他一贯喜欢出风头的毛病,本意绝不是要害阿黄姐姐。一边想,一边就走到了供销社院门口,但院里那种冷清,我不敢进去。
就死人这件事而言,阿黄一家表现与众不同。母子俩过于安静,没嚎啕大哭,也没磕头喊冤,更无露天陈尸以表达愤怒和冤屈的举止。九道沟人不适应这种死亡气氛,都觉不自在。阿黄母子的不动声色,令人担忧。那种本该是深夜专供鬼魂出没的静悄悄,大白天也散布在供销社的院子里。几乎所有那几天去过供销社的人都觉空气冰凉,想说什么话忘了张口,想买什么东西忘了用什么买。说不出话,是很容易忘事的。这就让人恍惚了。我在院门口觉得恍惚又害怕,想起了我外婆。
然后我就跑到电影场后面的梯田梗上坐着,摘了枝紫云英放口里嚼。
这里正好面对两条河交汇的宽阔河滩以及汇成一条的河水转了个大弯再进入逼窄的三倒拐的视野区域。对面是九道沟最开阔的一处河滩,有大片沙地,适合种甘蔗。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的,那块沙地就长着甘蔗。我寻思小五斤如果要躲他爸,藏在甘蔗林是好的。林子大,躲得开,还有甘蔗吃。
我跑下几十丘梯田,还没过河呢,就见小五斤站在甘蔗地边上招手,阿华阿华地喊。我哈了一声朝他跑去,他闪入了甘蔗林。
我们聚在甘蔗林里了,他开心地说,你在电影场背后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我念了咒语,你就过来了。你看得见我啊?透过甘蔗缝,我看了看电影场,刚才我应该坐在砖墙的影子里,要看清楚可真不容易。你念的啥咒?他说阿华快过来华快过来。这可以吗,我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他说,我们之前没搞懂,乱七八糟的念。咒语就该直接喊名字,哪里用得着刘幺姑那一套。真的啊,我惊叹道。当然,他问,你有没有觉得非过来不可?啥都拦不住你,非过来不可?觉得,我说。我撒了小小的谎。应该的,我觉得小五斤需要我这样说。因为我们是生死兄弟,生死兄弟有神力,他说,生死兄弟太金贵了,神仙会给力量到生死兄弟。对,我说,我们是生死兄弟。所以呢,我想,我和小五斤的关系升级了,比朋友还金贵,代价是阿黄的姐姐死了。不过我不应该提阿黄姐姐的事,这事太没法说了,只能以后再想办法说。
你以后想要我来找你,也朝我念咒,不管天远地远,我一定赶来找你。不过你不要念小五斤,也不要念刀发魁,我爹给我起的名字都不用了。我改名字了,刀牧,以后你要念就念刀牧。
我便劝慰他,你爹找你三天了,今天还来我家问我。打一顿就算了,你不是天天挨你爹揍的么。
不是这个问题,他说,还有就是阿华,你不能给我爹讲找到我了,你要发誓,绝对不说。我没吭气。不是不能发誓,而是不明白。
他逼我,你必须发誓。我说,干嘛!他说因为我们是生死兄弟,我说啥你都得依。你说啥我也会依。我反问他那我要说我不发誓呢?你依不依呢!他说要讲先来后到嘛,我先要你发的誓。我问他,那么以后你是要自己回家么?他说不。我急了,咋滴嘛小五斤!他说我决定了,我要去找老紫金洞挖金子。等我挖到金子说不定会回来。我吃了一惊,现在就去啊?按理说呢,我该带着你去,他说,你太小了,吃不得苦。我说等几年我们一起去啊。他说等几年你就读书考上学校了,以后吃皇粮,哪里还是去挖金子的人。你学习好,你爸都安排好了。你以后又吃皇粮又当作家,我听你爸跟我爸讲过的。说你的作文比他还写得好呢,将来肯定是个作家。你爸是大文人,还教你不出来啊。所以呢,我们两兄弟迟早要分开,你注定不能去挖金子。晚痛不如早点痛,早痛还不如现在就痛。我早就想清楚了,一直等你来跟你说一声再见。
我说,你一直在甘蔗林里想啊。他点头道,你来了我跟你说清楚了就好了。
走上了一条故事线,冒险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