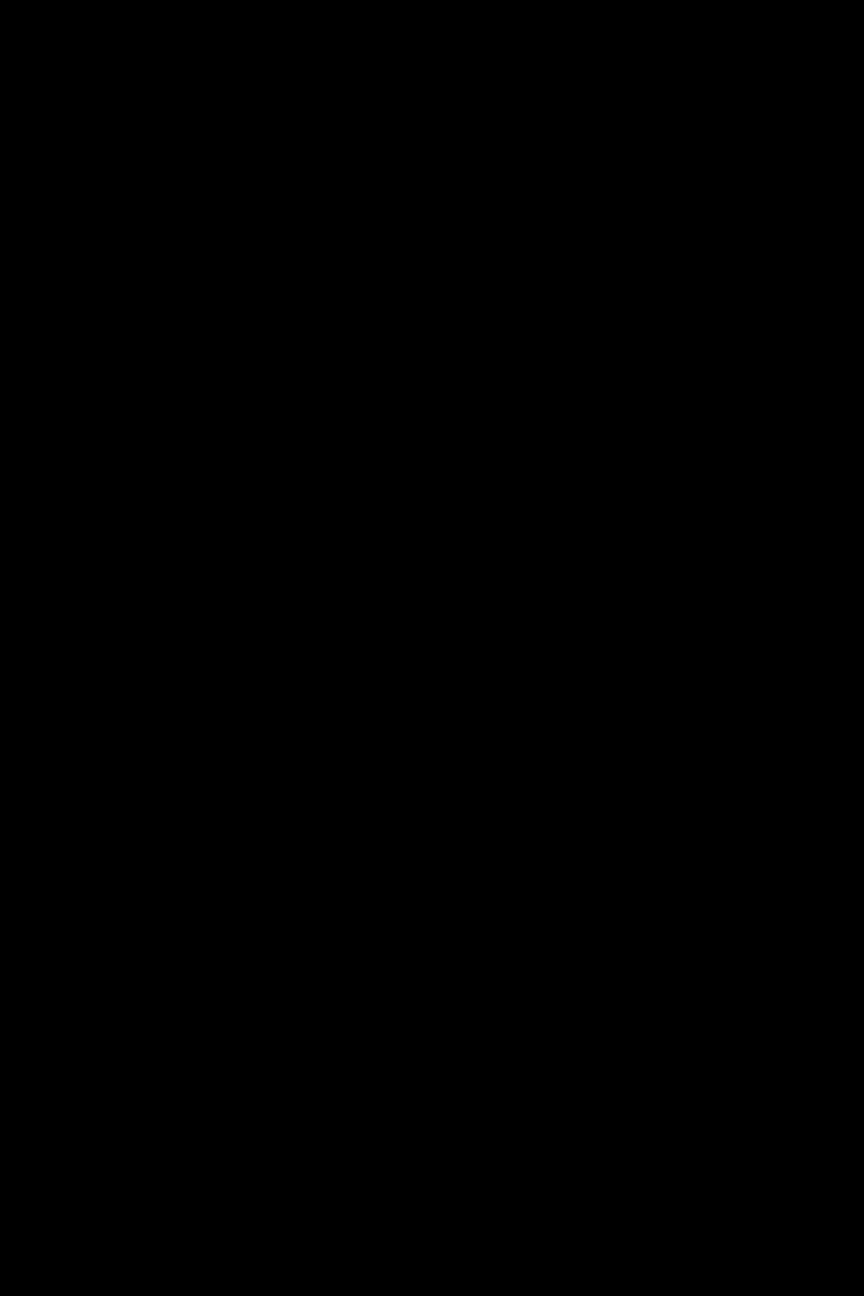热天午后(修订)
热天午后
大概是夏天。白昼很长。吱吱、滋滋或丝丝。声音。不知啥时有的,也不知道啥时无。像是白昼的一部分,入睡之前不可避免,醒来时也无法摆脱。我慢慢地细致地洗了把脸,特意用牙刷把挖了挖耳朵。不过我并未抱希望,也不想撞运气。声音还在。既在空气中,也在我大脑中。所见即所得,没法想任何事情。
应该还是我,从洗漱间出来,见房正中有张大圆床。特别大,特别园,特别正中央。就像为浪漫大床所作的广告,床上有个少妇。她牛仔裤已褪掉了一半,却半途而废地望着窗口发呆。我既看到她黑色镂空丁字裤勾勒臀部的迷人情况,也看见她面孔呆滞地朝向窗口。于是有了两个线索,不确定该从那一处着手。另外,我想不起女人的名字。应该不是不认识的人,只是看见她的瞬间,名字从她身上消失了。当然,想不起名字也没关系,眼前的事并非需要从头开始捋。牛仔裤都脱一半了,我当然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但她注意力不在我身上,要我等一下么?等待的空隙,一般情况是聊几句。一般情况下事情并非如同小说叙述那般流畅,一般情况下世上的事,比如作爱,就得捎带聊天。我得和她聊几句。
她举起两腿,直直指向我。我揪住裤管,用力拉掉。可能,我还应该,一丝不苟将她的牛仔裤折好、抹平,工工整整地放在沙发上。我按我的想法做了。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则愈加正经地显得心中有数。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亲爱的,一男一女密室相处就是好,只有欢乐,没有斗争。我再次回到她身边。她将体恤掀到头顶,让我取走。我仍保持沉着,将体恤折好,放在牛仔裤旁边。第三,当然,我数着着呢。我试图让眼前的事有逻辑。她扭转身体,让我帮她解除胸罩搭扣。果然,在乳罩脱落的瞬间,乳房沉甸甸下垂,同时露出了整块背部。光滑柔和的一大块,好动人。如果形容词连续出现,说明我被感动了,于是我心悦诚服地贴上耳朵。当我的皮肤贴上她的皮肤时,我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专注。感觉这专注就要让我挣脱头脑中的嘶鸣了。我仪式感十足地移动耳朵,探寻找她心脏的位置。充满渴望,想听她的心跳声。心在肉体里震动,就像震动瓮里的水。希望有的。柔和、稳定,希望,我希望听到她的心跳声。
但她挣扎。吱吱!吱—-!还用力推我。我赶紧跳下床。咋啦?咋啦!吱吱。或是丝丝。哦对,嗤嗤。我弄痛你了吗?哪里?我翻动这个怒气冲冲的身体。
原来我们是要一起洗澡啊,我恍然大悟,那肯定是夏天啰,说不定是最热的时候,要洗澡,一起洗,怪不得一开始我就在洗漱间,所以我才会从洗漱间出来,我只顾洗脸,忘了放浴缸,应该是很大的双人浴缸,不是双人浴缸配不上浪漫豪华大圆床,我们该是选了周末,好浪漫啊,一起选了个周末,怀着逆反沉闷生活的冲动,冒险设计了浪漫,我们要最无忌惮地与陌生人搞搞,这个念头应该是女人,作践自己的身体便是作践丈夫的权利,女人才能为此兴奋,那么我呢,我还得负责浪漫吧,先往浴缸撒些玫瑰花,仔细近于虔诚地为对方洗净身体,百般珍惜地侍候即将献给自己的礼物,为对方涂上花草味儿的沐浴液,搂在一起,让皮肤对皮肤,说出仅有皮肤才能对皮肤说出的甜言蜜语,说不定浴室中过于充分的调情,会让我们多出一次性满足,我们已不小了,吃一顿少一顿了,这样说有点伤感呢,不过是事实罢了,抹上洗浴液,彼此弄得溜滑,一遍又一遍地,你在我身上滑过去,温存地,我在你身上滑过去,一遍又一遍地,我口若悬河,看见太多空白和停顿了啊,因为颅内的嘶鸣,眼前事物的景象都慢了半拍还不知,或者卡卡地,无声地闪烁,我竭尽全力地说话,说啊说啊,但别急,等等,我好像还想起一些事,是个情景,在干旱石砾荒滩,孤兀显眼地生着一丛剑麻,剑麻阴影不大,汗流满面的青年仅能荫凉他的半张脸,吱吱、滋滋、丝丝,声音与景象匹配,或是声音带出了景象,或是被入侵大脑的最后抵抗,看上去是西部片取景地,丝丝、吱吱、滋滋,疲倦的青年唯有力气动动沾满汗珠的眼皮,头却越伏越低,我始终未能看清他的五官和表情,不过,我知道他就要失水而死了,这个死亡的名字叫费尔南多,是这个死亡的名字,并非所有的死亡都会被濒死者起了名字,极少有人有灵感,居然给自己的死亡起一个名字,费尔南多,我想起了他所想,费尔南多,但我想不起这个词语的声音,虽然我肯定知道每个词语都有一个声音,尤其知道这个词是恰好是一个声音的名字,一个西班牙声音的名字,费尔南多,这个失去声音的词语,没错,这个即将脱水而亡的青年给他的死亡起了一个名字。他正在念着这个名字。
她打我了一巴掌。我本能地回击了她。打在她膝上。也不算重吧。有准备的情况下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冲动起来无法控制。应该是,她没想到我会回击,所以事情又卡住了。我说你不会把我们的行为当作调情么。调情啊。她半惊讶,半风骚地张了张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吧。自我们上床开始,寻欢作乐的模式便不可撤销地启动。事已至此,我们不得不下定决心。一旦产生了欲望,便需逮住机会,尽力组织条件,屏蔽干扰。那个夏季的有一天,我从洗漱间出来。我干嘛非要从洗漱间出来。就那样别扭着,上了女人床上。不会是看了卧具广告产生的想象吧?我拼命争取真实感。但有个声音占据了我,我毫无办法。对不起,我当时这样说。对不起。我就要从你两腿中间进去了。看上去只能如此,两腿中间,和一个想不起名字的女人。对不起,你是谁啊。天啊,我无法闭嘴。
吱吱、滋滋、丝丝。有一会儿我觉得我明白了,我拼命希望的是声音能具体到有物有事。远处的知了声,隔壁煤气管漏气的声音,深夜有个失眠者的声音,随便能联系上什么都行。别这么好像声音,又像与世无关,仅像是大脑皮质在慢慢撕碎。别给我这种痛苦,又不像痛苦,别给我。有时含含糊糊的撕裂感产生了波动,好像前一阵是后一阵的幻影。前一阵有些刺痛,后一阵有些变形。不过也算有了节奏。所以时间是有了些形态。就是那种节拍感。当然浩大白昼,依然一成不变。这种景象让我闭不了嘴。热而蓝的,他妈的欧美总裁拜访东亚总裁那一阵,为了世界和平特别制造的总裁蓝。窗外屋里都是蓝,没有时间存在的位置。发出声音的东西肯定有个名字,只是我讲不出来。就是那种感觉。讲不出一个东西的名字。我一边干她一边拼命表现这种无法表达的感觉。只是干。万事万物的表达都是干。她也是失去名字的事物的一部分。统一在一种或一系列声音里,吱吱,只是干。
然后,两具肉体受控于同一个动作,但获得的思想却不尽相同。只有疲惫是相同的。然后,我因渴望最后一击而猛烈抬头,而她受我激励,双峰高耸并将头拼命后仰。所以我们的两双眼睛,同时看住了离床大约一米五的窗口:那是高丽镇中央十字路口,两个男人正在互殴。确切地说,该景象位于整幅玻璃窗四分之一部分,右下角,一尺见方的铝合金格子中间。我们像在看一个视频。亲爱的那是两个男人在打架吗?她没空回答,若要回答我也只能听见吱吱声。我们正忙着呢。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她奋力滚动。我的意思是说,滚动的力量是从她开始,而她的意思是我必须保持插入并顺应她的力道一起滚动,因为只有两人保持并稳住结构,才能先用她的背再用我的背滚动形成所需要的那个园。
最后一幕:漂亮屁股终究因我的力竭而下垂。下垂瞬间,我慌忙托住。不,我只是惋惜,惋惜其形状的改变。终究屁股还是很蠢地坐床垫上了。我茫然收起两手。那么就这么啦。那么就这么啦。那么就这么啦。学舌饶舌。起先说这句话是想为事情的结束表一个态,重复一遍后我快活起来了。腔调带出些旋律。我快活极了。那么啦。那么啦。有一疑点是我们都没流汗。不是说天气很热么。那么炎热是视觉上的?或是记忆中的?知识里的也许吧。寂静倒是真的。耳鸣便是因为寂静。内外压力失衡。没有寂静耳鸣怎么显示呢?你刚才叫唤了么?吱吱。你叫唤了么?我则从头到尾都很镇定。感觉我并无欲望。没有激发欲望,也没有满足欲望,只有疯狂。但我们为什么非要借性事表现疯狂呢?故意不带套?也许吧。当我紧张观察,寻找体外射精的最佳时机时,她则(我想象她在说,射我吧,烫我吧。)现在,我担心她怀孕,想听她说说这事有没有关系。她要了一支烟。除了看见她抽烟,她别的信息都隐藏在吱吱声里。
时隔不久,我和女人被四个黑衣人押回高丽小镇,带入上次住过的房间。面对黑衣人,我们无法表示不满。我非常沉默,密切注意自己的大脑。生怕吱吱滋滋的声音会因故地重游而复发。还好,我听见黑衣人明明白白地说,你们所涉及的是黑衣人的秘密调查,懂吧!我们连连点头,兹事体大。女人走到玻璃窗前,指着玻璃窗右下角方格子。咱们只在这里看到的,别处都没看到。她用指头沿格子描了一圈,表明一切都发生在方形铝合金框格里。比方说,就像看一个手机视频。所以呢。你们他妈的蠢到家了!你们他妈还是人吗!黑衣人一脸嫌恶。享用首都资源,不承担首都公民义务。他的话我们当然不同意,但无勇气反驳,就像所有普通人对黑衣人应该做的,默默地,尽量不显露表情。一开始就因女人姿色出众,黑衣人总拿眼睛瞟她,她便主动承担了与之沟通职责。那么你来我往地,只让我怀疑他们会当着我的面干起来。我们不是都在寻找刺激么,现在我可以成为他们的道具。黑衣人可以享受权力,女人可以再次作践我作为情人的权力。所以她说的有些话,在我看来,没必要说的,除非是为了和黑衣人调情。非法同宿的事、男女共浴的事、体内射精的事,等等,她越说越过瘾。黑衣人一脸鄙弃。真恶心!在伟大首都干外省人的肮脏事,等于犯罪!天啊,我的想象成为现实了,黑衣人就要在我面前和女人干起来了。我毫无办法,黑衣人和女人,权利和资源,我只是他们表现权力和资源关系的见证者,他们必然会当着我面肆意妄为。但是,我热切的,逐渐冒汗的想象嘎然而止。因为静静地,窗口出现了两个中年男子,梦游一般地走近对方,手里都拿着板砖。
根据黑衣人对蓝衣人的交代,我获得了更深刻的背景知识。原来窗内的景象比我和女人的周末更古老,原来这事并非只发生在窗口,而是在更辽阔的世界了。很久以来,京郊高丽小镇,网红旅馆楼前,十字路口的正中央,每天正午,都会出现两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各持板砖拍打对方的头部。就像重复播放的录像视频,没办法关机。每天正午都会出现。四周都封锁了,仍然无法确定准时现身的男人来自何处。他们无法停止,非得打死对方。逻辑上来说,总得有一个人先死,那互殴才会停下来。先死的人死了,随后的男人受了重伤,费力将自己翻转过来对着天空。在纯粹无杂质的蓝天下,使劲冒泡。泡冒完了才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