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电影院醒来
#我在一个电影院醒来
我在一个电影院里醒来。银幕上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少妇,将一崭新自行车放稳。用她棕色长靴,轻踢支架。准确、机敏、有力的触感传到我身上了。我被感动了,我好像就是那支架。她身材很好,让我产生形容词。此时我就是一台词语生成器。我因形容词而感动。我是如此渴望找到一个词,以便捕获并储存那正在消失的美妙。或许是曼妙吧。曼妙的声音更好听。不过最终画面还是在我眼前,虚化并消失了。在一种类似微风拂过银幕的轻柔旋律中,中音提琴相似的,略显沉降的共鸣中:本片结束,谢谢观赏。这是什么电影?场内含我仅有两人。另一个人,在尾声中,只是愈加幽暗,无法被干扰。我的姿势与他一摸一样,身体以臀为转轴,折成九十度,两腿长长地,伸入前排椅下。我理解的是我被卡住了。如果我不想起身,并无卡住的感觉。但我能理解,毫无动机支持我起身的情形,就是被卡住了。我是真的醒了吧。如果是,前提便有个入睡。可能没等到电影开演,我便睡着了,醒来只看到结尾。一个少妇。应该是用了她的脸,连带她的胸,讲了故事主要,现在用背影来结束。所有事物的正面都富有戏剧性,尤其是少妇。她有柔顺雅致的身形,让我断定是个少妇。少女变成少妇,一定因为一位或两位男人,故事还是这样老套吗?我不知道现在的事。两秒到三秒,她用一条腿,用一支靴子后跟的侧面,将自行车支架踢到位。那条腿修长,匀称。描述形态就是描述感觉,这些形容词,反复回传助我燃起微弱欲望。但还不够支持我起身去找欲望变现的方法。她腿扬起时臀部明显兀起,于是我注意到臀部,于是,臀部又随腿的下降而缓和了线条。多么柔韧的臀部,弹性十足。我从臀部的形态揣测她很健康。经期正常,没有白带,消化系统不错,心肺精巧结实。多么美好的臀部啊,我对另一个人说。不过得不到他的反应。看上去我的声音传不到他处。我说的是看上去。因为我也并未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习惯了说话这个词,忘了某个时刻,在电影院,氛围充足到不用消耗物质媒介便能传递信息。此时此刻,我们使用的是意识语。此时此刻,我们不传递信息,我们被笼罩在信息里。可以一次用到准确的词语么,我做不到,所以有句子。现在,有着漂亮臀部的女人已于十三秒之前消失了。我和另一位观众的失落,失落的时刻,补足失落的想象,应该完全一致。不然为什么电影里留下来的只有我们两人,不然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人在越来越努力地相似而没有其它?在我利用词汇保留感觉之时,浑然不知放映机早已关掉。这也是一样的。我们眼前的屏幕已不是屏幕,只是视网膜上一个特别黑的区域。还要等一等,它的黑才能与四周的黑调均匀。我怀疑另一个人睡着了。或许他就从来没醒过。而我,心有灵犀地,觉得自己也最好像他那样。慢慢地,等黑暗淹没我的思想后,重新再睡去。这样我便可将我的醒来,当成是重新开始的梦。这样我便不考虑分叉,不担心选择,单一执着地流淌。也不一定用流淌一词。用洋溢也行。我调慢呼吸,等待着,不再使用词汇。固执地,等待。老实说不让我使用词语,一分一秒地,很难受啊。因为我他妈其实是个作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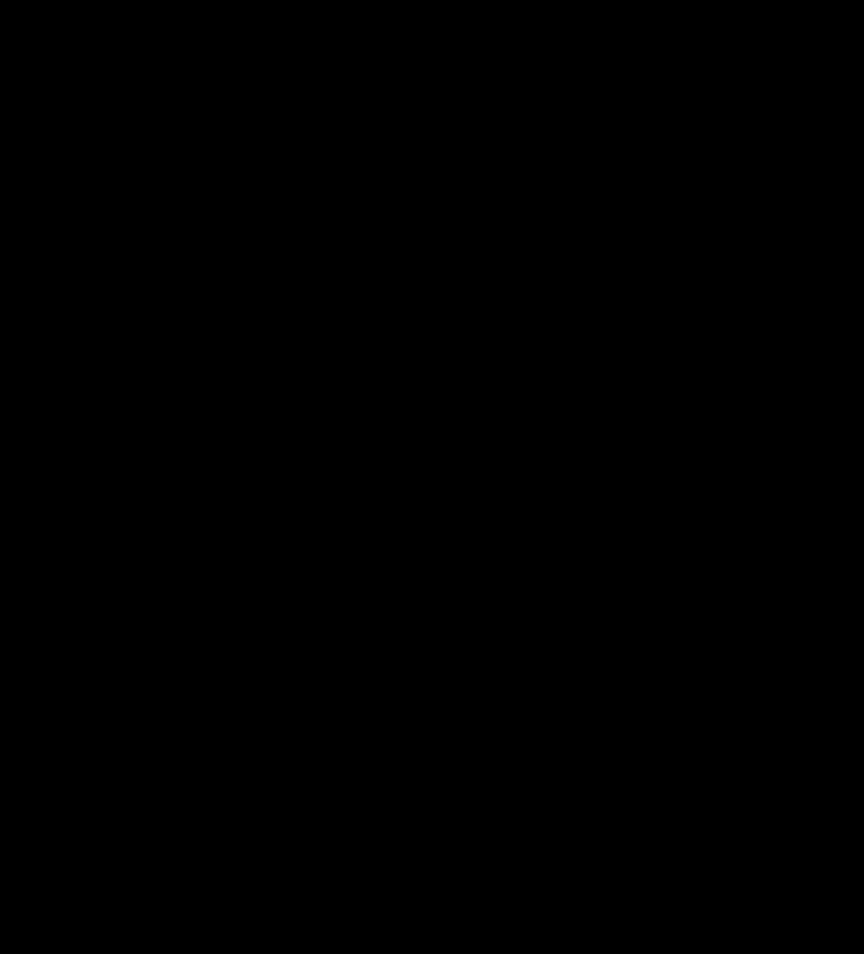
🤮:单一执着地流淌
(dbq这个笑话不好笑。喜欢这个表达。)
#我们,神们(借用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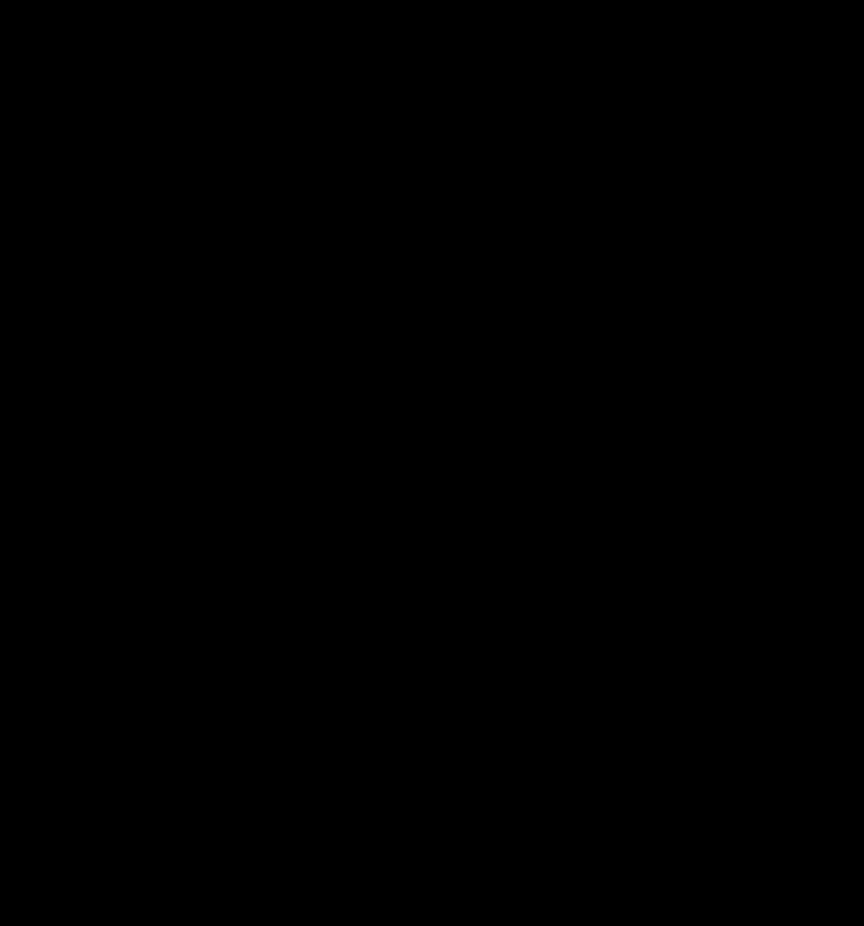
也是我,和一个女人被关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我全身赤裸,四肢往后铐在墙上。面对女人,摆出达芬奇所作德鲁威人造型。我只能直端端对着女人,无法选择别的形式。女人也赤裸的,抱膝蹲坐墙角。有个蒙猪八戒面具的壮汉进来,用电棍杵我的前额。滋滋的电流声、皮肉烧焦的气味,满屋都是。我昏厥后,他强暴女人。女人已在恐惧中屈服,相当顺从,甚至主动作出一些颇显诚恳的媚态。到头来我忘了痛苦,忘了屈辱,忘了愤怒,没心没肺地性欲大作。猪头心满意足,哈哈大笑而去。每天如此。你叫啥? 艾娃。你呢? 她这一反问,我愣住了。我叫华秋么?显然不对。瞬间我注意到自己身处一个梦中。一个梦的内部。比如,痛苦的感觉并不确切,好象痛苦只是一个词;比如,我明明是昏厥的,却将女人与猪头的作为,知道得清清楚楚;比如,一开始我便意识到“每天如此”,这个经验非常确定,却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一定是个梦,因为人和事均不是感觉出来的,而是叙述出来的。一定是那个名叫华秋的人做的梦。不让我怎么会一口喊出这个名字。我应是他梦中一个角色,也许是他欲望的化身。我想起华秋,却不能说就是自己。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艾娃说,有了名字才好聊天。好。尼鲁。尼鲁不错,让我觉得我就应该叫尼鲁。尼鲁——。我沉吟一阵,却未想出什么尼鲁不错的根据来。艾娃,我们是怎么回事?怎么被关一起了?这不就是个梦么,不奇怪。猪头是谁?他怎么敢这样对咱们?不认识。也不知道。这样啊。艾娃,尼鲁,看上去还不算太糟。我都习惯了,我常被人梦,然后就到了梦中。从来不清楚是谁做的梦,也没法知道每次梦中会遇到谁,不过我知道所有梦的结果。什么结果?她嘻嘻笑了。我若有所悟。我是艾娃啊,你忘了么?万物之母啊,艾娃就这样。这样啊,大数据显示,艾娃是全球女孩最爱十个名字中排列第二的名字。艾娃,你能帮我么?帮你什么?我没好意思说出口。不过我全身赤裸,摆出德鲁威人的姿势。四肢后拉,腹部前倾,突出之处那么明显,需要她帮助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帮你什么啊!她调皮了。啊呀,我说,瞧瞧你,没男人受得了!我很漂亮吗?绝世美女。于是她开开心心地过来帮我。估计本文会在网络发布,此处省略数万中文字以及数亿BT信息。事后,我问,明天来的还是猪头么?她摇摇头,来什么都无所谓,世上流行什么装扮跟我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她回对面墙角抱膝而坐。我们一起等明天吧。很神奇吧我们认为我们还有明天。这个荒唐的梦,其实也挺有逻辑的。假如一个封闭的不见天日的空间里,仅有一男一女,显然的变化即是第三者登场。以人际关系的变化和转折计时,挺合理的。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假设事情的起源其实是相对复杂的三人局面,次日走了一人,剩下两人等着重回初始设置。事实上明天是昨天的轮回,昨天是明天的轮回。只是今天,今天只是基于昨天对明天的等待。如果我有耐心写这周而复始,写这毫无新意的轮回,会在第三或第四个轮回改变角色属性——我们,其实是神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