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地方 #那个奇异的晚上(修订)
那个奇异的晚上,他怎能忘记!大概是凌晨三点,他被一阵猛烈的喊声惊醒。那喊声是这样说的,赖彦明,你己被包围了。放弃无谓的抵抗,马上投降!喊声之后,传来拉枪栓的声响。太不可思议了。他以为在梦中,所以没动。他妻子迷迷糊糊问,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这时那喊声振动窗纸,伴随嚓嚓响再次传来:赖彦明,你己被包围了。放弃无谓的抵抗,马上投降!他想起了演电影,那些年常有电影台词与此一摸一样。那声音说:马上投降!现在,我数到十!紧接便气势汹汹地数数了:1,2,3。妻子说:快投降!于是他赶紧说:我投降。生怕外面的人没听见,他又用了更大力气高声喊:我投降!那声音说:别搞鬼!你已彻底被包围了。
他手脚忙乱地起床,这时看见五个月大的孩子冲着墙蜷成一团,睡相非常动人。他差点又迷惑了。还是梦吧,躺着不动就能对付的那种梦。妻子还在问:怎么回事呢?他说:先投降了再说。也是,妻子说,先投降。
他高声说:我已经投降了,我穿好衣服就出来!
他穿好衣物,打开屋门,一道五节电池发出雪亮的电筒光立刻照在他脸上。好一阵等视力恢复了,他才看清是三个人。三个人手里都有枪。
一支驳壳短枪,两支上了刺刀的长枪。驳壳短枪持有者是公社武装部的白部长,刚才他通过一个塑料话筒凑在窗纸上喊话,声音变了形,所以没能听出来。他说:白部长啊。怎么回事?白部长没理睬他,拿短枪的那只手挥了挥,另两个人便迅速平端长枪跑到他身后站定。
他一转身,他们亦马上转动,好象两支长枪是长在他后腰上的辘轳把似的。
妻子捧着油灯出来,惊叫:屋顶上还有人!白部长得意道:后门还有呢,这一计叫瓮中捉鳖。出来吧,战斗接束了。后门边矮墙上便敏捷翻下一个人来,走过来很不满意地说:这样就算了?白部长想了想说:那就绑了吧。
他们拿出绳子,三人来绑他。三个人一齐动手,都兴奋异常,把他弄得痛出了汗,叫了一声。妻子慌慌张张地连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随即她看见院门边躺着被这些人毒死的狗,哇地哭出声来。一个人对她说:这阵就哭!怕还有不够你哭的!她便不哭了。白部长说:走。于是他就被他们押着走了。
他当然还记得,那天晚上的田野上,有很多很大的星星。
星星的出现不是为了照耀,而是为了显现古老痕迹。是的。认出这些星星的虫子,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叫。他仔细听那些虫子,觉得只要能在夏夜的田野上走动,都是很快乐的事。因为这种快乐,他至今不能确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忍心破坏星星和虫鸣间之间的安谧,没对刘部长等人提任何问题。那时间他为某种超越人世的情感而淡望了世间的角色,所以那时间他把那些抓捕他的人都当作了一起散步的朋友。
(我觉得我爸是这样的人。)
他们走到禾家坪公社所在地,从一个人高举马灯照着的门进去。跟随马灯,进一间临时羁押室,他们要他交出身上所有东西。他交了腕上的手表、上衣口袋中的自来水笔,白部长很有经验地要他解下腰带,他明白他们怕他自杀,忙说:放心,不会。
马灯照耀下,他看清了白部长带来的几个人是成都来的知青,因水土一直不服,他们脸上的青春痘更多了。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她脸上用力地严肃着,因而冒着汗珠。
她曾捧着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向他请教。保尔和冬妮娅好浪漫啊。冬妮娅的白膝头。她含羞带俏,低头去笑。成都女孩的膝头也有值得上文学作品的白净吧。那是一分钟两分钟的浪漫,被他特别宝贵地藏在了心里。现在这个记忆的出现,令他异常疲惫。
因此等他们一走,他径直走向靠墙摆着的钢丝床,倒头便睡。第二天一大早,有人重重地开门。女知青送来一碗粥和两个馒头。她清秀的脸铁青着。他是个囚犯,而铁青着脸对她来说是一种职责。对此他很能理解,并开始担忧自己的命运。虽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安宁过,但象这命运如此直接了当改变睡床的事还是头一次。
但他依然忍不住愤懑,因为她曾对他专门显示过娇俏。他嚼着馒头,压制住情绪,故意不叫她的名字,声音冷淡地问她:同志,为什么抓我来这里?她朝他大吼:同志!谁跟你是同志!不准你污蔑这个词!她抬腿踢掉他手里盛粥的饭盒,破口大骂:反革命!死不悔改的反革命!
校党支部书记来时,他脑袋里还为成都女知青难以置信的暴躁行为嗡嗡地响。他怀着痛苦问书记:张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我是反革命?张书记的脸上浮出嫌恶,说他后悔介绍他入党,他后悔没能早看清他险恶的嘴脸!如果你还念点旧情,就忘掉我曾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最后一句几乎暗含威胁和请求,他无话可说。
快十点时,白部长带着另外四个人持枪站在门口。女知青不知何时也有了枪。她将步枪嚓地背上肩上,朝白部长敬了个礼,朝前迈出一步。原来她在完成押解犯人的仪式。当然,犯人就是他。他终于大体明白自己的处境了,现在他要加倍注意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而他们似乎不能容忍他里面潜藏着一个超然的观察者,所以用很粗的绳子将他绑得很痛,并往他头上扣了一顶近三尺高的纸帽。他仰头想看清纸帽上写的是什么,女知青便打了他一耳光。
他被押到学校操场。操场已集合了政府、学校、供销社、卫生站、收购站的全部职工,还有不少农民和学生。面对潮涌而至的人群,白部长率领的押送队伍不由自主地迈开了正步。而他,不得不显得猥琐了。显然头上的尖尖帽非常有效果。
操场一头是插着旗杆的三层水泥台,另一头并放着两张课桌,他被押着去向课桌。有人说:干嘛给反革命份子两张桌子!于是有两个学生便跑去抬走了一张。他费力地爬上桌上站定时,看见妻子孤独而绝望地站在人群里。当时他想,自己不可避免要与她分离了。
张书记问他:赖彦明,转身看看,认得墙上的字吗?他转过身,看见自己用排笔写在围墙上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批判的武器”一排大字。张书记大声追问:认得吗?其他人都凝声静气等他回答,他说:认得的。张书记问:是你写的吗?
一个月以前的一天,张书记说,小赖啊你看咱们围墙空着等你秀字呢。他排笔字写得最好,历来负责学校宣传事务。他写了这排字,抽着张书记递来的烟,与之并肩而立,颇有古风地含笑赏析。那一刻多美好啊。他怀着不解,不晓得怎么回答。不过他最终还是生怕因为自己的节外生枝而错过什么,因此干脆地说:是我写的。人群顿时传出恍然大悟的喝的一声。听到这一声喝,他连忙再次仔细看这一排字,看了三遍,它们都是整整齐齐,气派十足,一笔一划都是标标准准。
“黑体是在现代印刷术传入东方后依据西文无衬线体中的黑体所创造的。又称方体或哥特体,没有衬线装饰,字形端正,笔画横平竖直,笔迹全部一样粗细。虽然没有什么笔锋可供玩味,但却异常适合无产阶级雄壮、有力、肯定、直接-----。”
张书记用一种气愤得变形的声音说:那么,我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请你把你写的反革命言论念一遍。这是反革命言论?他被吓住了。而身后传来粗暴而低沉的怒吼:念!念!念!他大汗淋漓,死盯着那几个字发呆,不明究里,而他们继续整齐有力地怒吼:念!念!念!他知道这种声音。物理学上讲一千个人整齐迈步所发出的声音会从一座桥的内部彻底让它坍塌。他明显觉察自己正在坍塌。坍塌感在他的骨骼里直坠下去。这种坍塌感穿过时带走了晃晃悠悠的眩晕,彷佛是对他自从被五节电池的强光照过后所感到的不适的一种解脱。毕竟它朝着确切的方向,毕竟,尽管它是绝望、不可遏止的下方,毕竟。---
于是他定了定神,坠崖般地高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
他们应声涌来,推翻了桌子,将他狠狠摔倒地上。白部长挥着手枪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场面已经失控。他跌到在无数拳脚之间。那句话尤如附在他舌头上的咒语,他不停重复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是………。
然而更让他惊讶的是,批斗会一接束,就有一个真正的公安人员两个身穿四兜干部服的人以及一个记录员,坐在党委办公室里等他。他们坐在四幅肖像图前面,让他心神不定。不太分得清肖像画的表情和四位活人的表情,只觉对面挤满了眼睛。
他们宣布:“三二恶意攻击领袖案”审讯会现在开始。
三二案件?他完全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他的事。他们的意思是,他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这一排字写上学校操场边围墙那天是三月二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三二案件”就在那时发生了。听起来好象三月二日是早就埋伏在时间的单独阴谋,而专案组亦早就成立了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天,他提着油漆桶和排笔,爬上桌子,写了那些字,于是“三二案件”就在这个横断山深处的小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发生了。老实说,群众们情绪剧烈地将他掀下桌时他并不觉得疼,奇怪甚而略有醉意地,他有一种被深深感染后的头晕流鼻涕的症状。但现在,新的名词出现了,“三二案件”。竟由自己所创造。难道这是历史。他深深地震撼了。也许时代变了,时代终于转头冲着我来了。所以我们说,紧跟形势调整帆舵是任何人都马虎不得的。那时候他们每周都有两次开会讨论形势,既怕出岔子,也因为孤独。他很诚恳地想:时代变了,但他没接到通知。
穿警服那位面容和蔼的人叫黄公安。黄公安对他笑笑,问他:你为什么要攻击毛主席思想?他说:我没有啊。黄公安立刻收起笑容,表示对他的厚颜无耻感到恶心。这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大汗淋漓。
黄公安说:赖彦明,我看你并不像一个无赖,铁证如山,你怎么能这样呢?他摇摇头,表明他不是一个无赖,但他的确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多人一口咬定他攻击了毛泽东思想,其实他伤心极了。
好吧,黄公安说,也许你是一个所谓的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你凭什么要批判毛泽东思想?听他这样一说,他明白了,原来还是那在那句标语上,可以解释的,是个语法应用,他心中踏实了许多,便慢慢给出解释:他写的标语,意思并非要批判毛主席思想,而是当我们进行批判时,毛主席的思想是我们用于批判的最有力武器。这里面有个语法运用,他是语文老师,当然知道,错不了。
黄公安似乎听进去了,很认真地问他:你要批判什么?他摇摇头:并非我要批判什么,而是我们,我们一定要批判一切有害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为。黄公安旁边那人看来再也忍不住了,猛拍了一下桌子。黄公安摆摆手,对他说:看到了吧,坐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么狡猾的敌人。
你很会隐藏,你的灵魂……。黄公安稍作停顿,意味深长:灵魂总是隐藏得很深的。而你,有一个狡猾而用心险恶的灵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黄公安的话让他觉得玄机无穷,当“灵魂”这个词出现时总是这样的。
黄公安这人面目和蔼,用词文明,甚至会让他产生幻觉,认为自己可以和他象朋友一般地交谈。谈的是灵魂这种玄妙问题,从学术层面讲,自有一种乐趣。但黄公安似乎只是简单地感叹了一下,转而问起了他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份、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卷宗上早就明白写着的项目。他也按卷宗上的记录清晰明白地回答了一遍,审问便被结束了。第二次审讯还在同一个房间,不过对面墙上,四个肖像画下,新刷着八个加粗的黑体字:坦白从宽,抗绝从严。字不错,九道沟除了他,还有谁能刷出这么标准的黑体字?怎么想也不可能还有谁。
他再次回答了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份、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因为八个黑体字横在面前,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十分慎重。完全不觉得是一种重复。
八个黑体字带来正式审讯室的严肃气氛,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为此下了决心要好好配合他们认真研究自己的灵魂。
这回他也注意到记录员是尤其重要的。他坐在他右斜对面,面无表情与众不同,是一层厚重苍白刷出的面无表情。黄公安提问,他回答。黄公安和他都会停下来静听记录员记录在案的用笔声。等记录员表示记录完毕,黄公安再提下一个问题,他也好整以暇地再次回答。有个记录员显然是必要的,会带来一种节奏感。关于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份、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记录员先对照他前后两次的回答都没啥差池后,将那两张纸递到黄公安面前。黄公安一支压着纸,一只手用拇指撑住前额,细细观看。他看得如此仔细,以至于他旁边的干部忍不住伸长脖子,也将脸往纸上凑。但是黄公安突然就看完了,将纸往前一推,那位窥视者吓了一跳,连忙坐正身体。
黄公安问:你的姓名叫赖彦明,对吧?他说:是的。黄公安说:你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是多么重大的日子,而你竟然起了个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是个问题吗?他问:我的名字有问题吗?黄公安说:表面看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看看我们的名字。我叫黄爱国,他叫林建军,再看看你的名字。你真的不觉得没有问题么?他想了想说:这是我妈起的名字。我妈是贫农,没啥文化。黄公安说,没文化的人可不会起什么赖彦明。他掉头向记录员:一般情况下,审讯室里只要求犯人在“是”和“否”中选择,我们无意破坏规矩。但我们现在审讯的是一个狡猾的反革命,一个须从灵魂深处最终获取罪证的复杂案件,所以要走点弯路。
记录员脸色苍白地连连点头,犹豫着要不要记录黄公安的这句话。是的,他在犹豫。他终于想出了主意,撕下一张纸,单独写下来了。
黄公安说:就算你妈没文化,但你是一个伟大祖国培养起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那么……,他停了停,加重语气,似乎在提醒记录员注意。那么,你为什么不改名字!记录员的钢笔飞快地摇动起来。他兴奋了,快速记完后大眼不眨地瞪着他。他正要说话,记录员惊叫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愣住了,不过,他很快明白了。记录员还年轻,过于激动了,这就像不小心碰掉个杯子一般地无伤大雅。
他说:我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理所当然就叫这个名字,我为什么要改呢。
为什么要改呢,黄公安重复了一遍他的话,说问题就在这里。按你的履历,你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被伟大祖国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民教师。你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竟然无动于衷,竟拿那你说的理所当然不作丝毫改变?他竖起一个指头,指向他:你那理所当然的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如果他没听错的活,他加了个“到底”来强调那个“理所当然的里面”。他觉得惊奇,因为他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来强调“理所当然的里面”。
他惊奇着,因而露出傻样。他不得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而他们亦目不转睛地将他望着。记录员都紧张到出汗了。他在什么时候应该也出过汗,不过现在没有,现在他只能默默无言地傻看着他们。
审讯一接束,他顿觉无聊,象站在个没底的地方一样。他躺在行军床上,通过门上的栅栏看外面被分成一条条的阳光和其他东西。阳光在栅栏间很亮,亮得只看见阳光而看不见其他。发现这一点,他就盯着阳光使劲地看,看了很久发现它们原来还在那其中,隐隐绰绰的:院子、院子对面一楼和二楼四道黑而静的门,还有一辆很少见的吉普车。他猜想自己很快就要坐那辆吉普车了。它在九道沟的河沟里一定跑得很棒。那时候没有公路,只有这种吉普车能沿河开入九道沟。
他望着吉普车想了好一阵,又看出视线里还有一个人的影子勾着头打瞌睡。那是成都来的女知青,下巴尖的影子指着胸脯的影子。这个面容清秀的成都女知青原来还有一个不错的胸脯。她会不会跟着他一起坐上吉普车呢?看起来女知青很喜欢世界上有反革命,那样她就不寂寞了。那样她纯洁的灵魂就不寂寞了。
他记得自己每次醒来之前,都伴着粗暴而剧烈的声响,好象他的沉睡由一道生锈铁门锁着需要暴力才能打开一样。正因如此,他每次醒来都因受到震撼而头晕。这次他看见妻子站在面前,边拿出饭盒边说:他们抄家了。乘女知青看着别处,她很快地说:他们要我交待我们为什么结婚。他吃了一惊:这关灵魂什么事?妻子愣了愣,后来她觉得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他们啥都没说,他们还用得着说吗!接着,她说:我成份不好。害了你!他说:没这事。她还唠叨:我成份不好,我害了你。她又低声哭泣。他烦躁道:我的灵魂和结婚没关系,和你的成份更没关系!妻子迷惑不解,止住了哭,想了想他的话,以为他不爱她了,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又想起点什么来:哦,你是想保护我才这样说,你还是爱我的。
妻子显然没法理解他的感觉,其实他的感觉自己也觉新奇。因为他平时有口无心地大说特说灵魂一词,“从灵魂深处”什么什么的。其实作为一个无神论者,那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但现在因为专案组成立,甚至是专为他的灵魂而坐吉普车赶来,要研究他的灵魂。所以这个灵魂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但却异常地有力地存在着。他甚至,他觉得,因为灵魂他竟发现了成都女知青的乳房,甚至通过被她打耳光而与她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关系。
因为急于了解自己的灵魂,他迫切地等待审讯,但他们总让他惊奇。他记得他们问:为什么要混入党组织?他说他渴望进入先进。他们说:挺能伪装的。他们问他:混入党组织干了些什么坏事?他说开会写语录写社论标题。他们便大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后来的几天,既没有斗争也没有审判,他好象被遗忘了一般。这让他既担心,又觉得这种担心无聊透了。主要是无聊,无聊时他发现对面二楼的三道门从未打开过,也许那种黑和静就是永还不能打开的意思。
妻子准时送饭来。给她送来炖狗肉。吃了狗肉,他很想要她,她走后他又想要成都女知青。再后来的几天,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见。不过他调整了对专案组的看法,认为自己并未被遗忘,而是被他们躲在暗处,观察着、揣摸着。所以他故作轻松,故意露出一些表情。
后来,突然在某个夜晚,他们出现了,动作剧烈地将他往吉普车上押。
先用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光照定他,使他无处遁形。再铐住他的一支手腕,由一个人先爬上车,拉住手铐的另一环将他往车上拉。而其他人则在他身后拼命推他。
他无意反抗,但他们认为恰恰相反。事实上他压根就没时间表现反抗或不反抗的态度,他们一出场就要求雷厉风行的效果。所以他已经在车上了。继而咔嚓一声,手铐的另一端已拷在车顶一个铁环上了。这种手铐非常灵敏,一动便紧缩,灵敏而冷酷的机械力量象刀一样切入他的腕骨,他疼得身体发僵。同时有人用枪管猛戳他的后腰,他惊跳起来,头重重磕在车厢上。当他终于全身被汗水浸得冰冷冷地,姿势难受地坐在车厢右侧凳子上时,身上的狐臭味便浓浓地散发出来。
这狐臭味使他心灰意冷,什么话都不想说。
有三个人押着他。膝上都放着枪,其中一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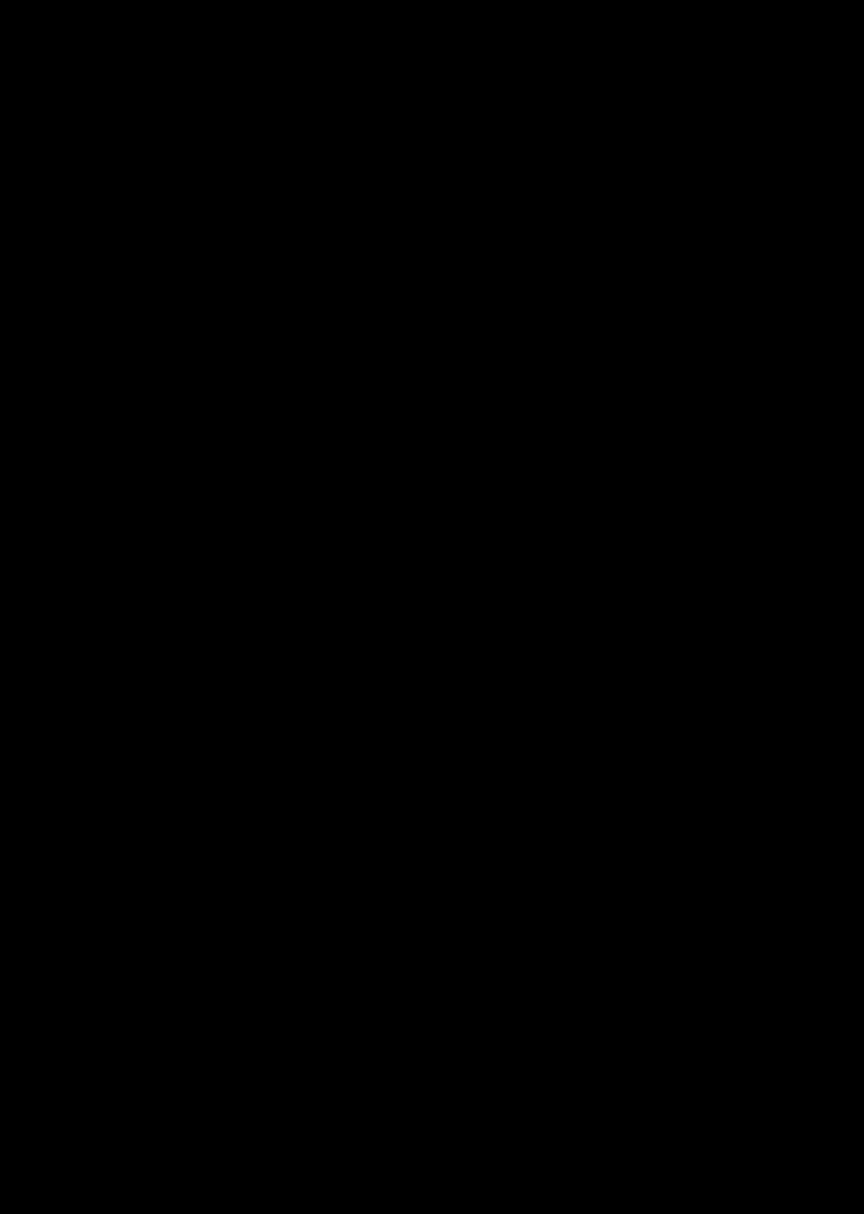
那女知青。
于是,吉普车就在山村夜里,发出很大的隆隆声奔跑起来了。手铐的灵敏甚至是神经质的,车体每一阵动荡均化作它环扣的紧缩。他汗水一阵阵地流出来。他空着的那手紧紧挽住被铐住的那只手,全身肌肉绷紧地侧坐着。他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只知道每一阵动荡过后,总要痛出一身冷汗,总会随冷汗涌出一股浓浓的狐臭味儿。
为了克服狐臭,两个男的抽起了烟。于是女知青受不了了,捂着嘴要求停车。
她跳下车,弯着腰呕吐,另两个跟着跳下去,拍她的背,往她前额上抹冷水,同时用最恶毒的脏话咒骂他。
他心中充满歉意,可是他很累。如果他没理解错的话,他们故意颠三倒四让他肉体痛苦、劳累,是为在他放松戒备时找到他的灵魂。他们认为他的确藏得有那个灵魂,那个在他不知情的状态中与“三二案件”沆瀣一气的灵魂。但在极度劳累中他散发出恶臭,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他的确想对那个女知青说声对不起,她真的很纯洁。纯洁到令他产生邪恶的性欲。但是他的确太累了,他的歉意模糊不定地和散了架的身体混乱地纠缠不清,以至于他怀疑自己就算开口道歉说不定也只散发一股狐臭。
人在突然紧张之后会散发出浓烈体味,而在要死之前会胡乱打屁。他不知道他们捂着鼻子朝自己扑来,究竟想嗅到什么咬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