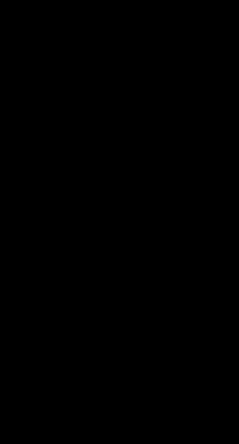拜帖。
这就有两层意思了。一、因过于神秘(在语言以外什么的),它本身不能够被谈论。其二、那只是一种人为的强制。两者我都没有默认与接受它们的必备道德与性格。但总归要谈,谈意味着一切且有限:这就算填上坑了。实在不行(硬谈也是一种品格),那就(实际上我们也只能如此这般不是吗)玄谈(即空谈的一种):一种安全但无效的非经验谈论方法。就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取消了功能(仅保留当地语法结构)的无效语言工具。我的运气一向极好,它们正好是现成的。十二月的玄谈庙,庙门敞开着,唯一的尼姑却不知去向,仿佛故意蒸发。整体气氛已不能用冷清、潦倒这类通用词汇去渲染美化,也用不着让一匹鹅倒挂在院子中央的树杈上沥干水分,没这必要。又或者召唤来一头熟悉的燕雀,停落在菩萨膝盖上拉一点喜庆的鸟屎以增添趣味。一个不再有任何动作的过气寺庙,仿佛已没有谈论它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它已被全部萃取精华且不可再生。它当然也是朝代(包括自身更替)的必然产物。曾有一度抚育、盘活了大批和尚,形同虚设后来也零零碎碎接济过几个落难尼姑。可见佛门之包容,并非外界说的那么强的排他性。可庙毕竟是庙。事物有起初,在一个统一时空中就一定会有它的结尾:每每到冬季,我仿佛总在处理类似的事情:结尾一部书稿或一年又一年养老送终之类。这已经无关个人情绪了,它是必要去面临无处不在的一个巨大事实。可以这么说,玄谈庙现在正当处于它最好的时候。玄谈(不是口语),它与空谈的本质分别,是它没有谈论对象。它也没有啥本质。两条裤子,两条裤子的裤边。当一篇著作中出现这类表达(我一般称它为叙述愿望),基本可断定那是作者在刻意玄谈。不是沉闷的娱乐,也绝非无聊(它太高级)与严肃的相互混合体。玄谈,一言以蔽之,一种不需要负责任的谈论技术。玄谈只关乎玄谈本身。而它本身却也是无论如何不存在可谈论的内容。在解放前,玄谈庙亦是如此。僧侣们作为完美利己主义者事务忙碌,知识贫乏,没工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不是他们要去掌握度日的方式方法。而诸如香客、居士、衙役之类游去寺庙,他们的动机无疑更为俗气。剩下无非也只有菩萨(不动与自由),为了排遣过于重复的冷淡景象,不得已只好热衷于此道。单谈那是没有办法。菩萨,晚上吃点什么?菩萨对着它的回音空旷问道。菩萨,晚上吃点什么?回音一阵一阵渐弱反问道。“东西带来了吗?”“东西带来了吗?东西带来了吗?”“裤边!”“裤边!裤边!裤边。”菩萨相互一问一答,仿佛菩萨对岸仍是菩萨。《一九八六年,小雪》。因为感到孤独,我时常退化成一只羊,少顷,又变化为一只贝壳,或一股气。其实不是。我只是突然变得不想开口说话。